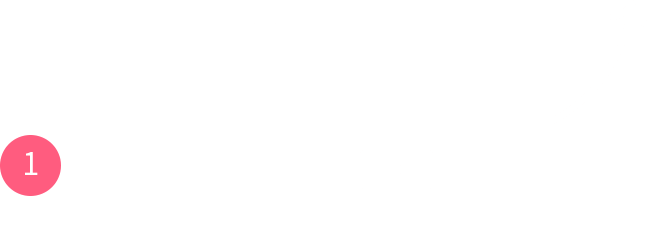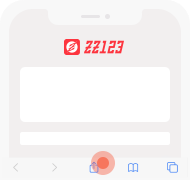布拉格之春
乐队成员: 主唱:尹达 23岁鼓手:戴征骏 23岁吉他:谢立治 24岁吉他:张安定 23岁贝司:储志勇 22岁代表作品:“癌症俱乐部”
认识这些复旦大学的另类分子是乐队组建之前的事了。
鼓手小戴当时正在疯子乐队的德国鼓手“鲍鱼丝”的打击乐小组里玩。而谢立治则是戈多乐队的编外成员。他们太沉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太酷,太清高。复旦大学的学院经历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在复旦方圆1公里的区域里,他们是最放松的。而出了这个地域,我总觉得他们有点紧张。但谢立治是个例外,他频繁参加各种课程,以接触到更多的女孩子,他乐此不疲。
“布拉格之春”与戏剧的关系也该讲一讲。小戴和谢立治都是麦田剧社的成员,这个短命的新生代复旦剧社在他们手里诞生,也在他们手里毁掉。搞“布拉格之春”,似乎是复旦戏剧界一件强强联手的高兴事。也许乐队本身并不能归进上海地下乐队的大事记里,但绝对应该收编进复旦戏剧史。“布拉格之春”呈现出来的似乎是戏剧的音乐。
谢立治一定要我写清楚“布拉格之春”的风格是迷幻+噪音。似乎这样才显得出他们的先锋与出世。“布拉格之春”的音乐确实很“出世”。凡是看过乐队演出的人,都是摇着头出来的。可不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太high,而叫人兴奋得摇头晃脑,相反他们的音乐实在没劲,太没气氛。可他们不管,自个儿在台上一个劲地软磨硬泡,折腾个半小时,便灰溜溜地下来了。可小戴却满脸堆着笑,说:“我们今天又激怒了观众。”接着耳边就能响起谢立治一串猥琐的笑声。这还不算,排练的时侯,小戴和谢立治创造了连续演奏70分钟迷幻噪音的最高纪录。而尹达写歌词,也总是拿出他写诗歌的劲道,“厕所”什么的,写了一堆。但有一点我相信,在音乐里,“布拉格之春”是自足的。他们更像支训练心理承受能力的研究小组,在冗长的音乐篇章里,配合环境、配合心境,在音乐上实践某种微妙的变化。(柳生) 布拉格之春--校园是根据地
用网上我们乐队的介绍说一下风格,通过别人的眼睛,算是避嫌。"在布拉格之春的音乐中你找不到任何乐队的影子,也正是丰富与简约,旋律与噪音的同时存在造就了一种阴暗、冰冷、压迫却又使人迷失于其中的音乐。乐队还是被外界更多认为是一支实验团体。"
写文章写到自己的乐队有时候是件很尴尬的事,而且说谁谁谁的音乐风格在现在是一个讨骂的事,因为好像每个乐队都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和卓尔不群。我们乐队从没有标榜自己,但做东西的实验性在上海确实有点另类。
不过,这篇文章用不着对音乐做过多的评价,只是交代一下我们几个成员的生活状态。 我们乐队是我目前了解到的可能是上海物质生活最充裕的一个乐队,因为乐队的几个成员都是从前或现在的复旦的学生。走出去,找一份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工作还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和我们相似的大概只有"惊弓之鸟",他们是一支从华东理工出来的乐队。 现在我在一家报社做记者;戴征骏在一个很大的日本的广告公司;谢立治去年辞去了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目前和还在读研究生的张安定一块全力备战GRE;储智勇最小,不过明年也该毕业了,相信工作性质会和我差不多,因为他读的是正经的新闻系。
我们乐队现在的阵容是由三支乐队拼凑起来的。我和张安定进校没多久就认识了,因为当时住的宿舍都在一层,彼此兴致相投,平常就在一起玩、喝酒、听音乐,有一年 Kurt Cobain祭日的时候,我们还一块连续出了三期海报寄托哀思。
张安定最早去学的吉他,当时是从师刘海深--当时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演示会上能时不时用牙齿咬琴,把我们都震呆了,不过现在想最没意思的就是这种炫技的Solo。他现在在复旦旁边开了一家很小的琴馆,主要还是靠教学生维持生计,已经很长时间没了他们要演出的消息。
大概是98年初的时候,我、张安定和另外两个朋友泡饭吃了半年,终于攒足了买电吉他和电贝斯的钱,又搞了一个小鼓,四个人算是凑成了一个乐队。后来一个人退出了,剩下我们3个,还是充满了激情。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学校的一个小篮球场上,演的 NIRVANA的歌,当时我还在弹贝斯,没有鼓,找了当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用鼓机做。现在这个朋友在华师大后门开了一家琴行,用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叫"李奇琴行"。很久没联系了,主要是复旦离华师大太远。
最初的时候,歌都是我用木琴先写出来,然后乐队再排,但终究因为技术和能力有限,那些歌现在看太稚嫩。过了几个月,原来做主唱的朋友也离开了乐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只能没事的时候坐在校园里的草坪上唱唱民谣。 后来认识戴征骏和谢立治,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学校了做戏剧,他们是"麦田"的人,我是"燕园"的人。他们也是刚刚散了乐队,也剩下两个人。所以,四个人凑成了现在的"布拉格之春",我把贝斯交给了谢立治,当上了主唱。
四人阵容开始后,乐队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大家虽然在音乐上各有各的想法,但平时排练是还是统一在类似Joy Division的"后朋克"和Pink Floyd的"迷幻摇滚"的基调上。乐队就是这样,不同观点只能在统一风格的基础上保留。要不,几个人在一起整天吵架,音乐没法做。
认识现在的贝斯储志勇,也是因为住在一个楼里,我和张安定在楼道里唱歌,他常下来看。后来我和张安定找他在我排的戏里做演员,又一块做了戏的音乐,大家熟络起来。后来他们原来?quot;朋克"的乐队"地洞"解散后,进了我们乐队,把谢立治解放出来做另外一把吉他,我们做的东西更自由也更丰富。
后来的演出还是挺多的。因为乐队后来做的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大家习惯互相看对方的暗示,所以形成的演出风格比较奇怪,除了我这个唱歌的人,大家基本上都背对观众。后来我也干脆唱着唱着也转过去。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排练了,大家都太忙,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阵容还能维持多久。
认识这些复旦大学的另类分子是乐队组建之前的事了。
鼓手小戴当时正在疯子乐队的德国鼓手“鲍鱼丝”的打击乐小组里玩。而谢立治则是戈多乐队的编外成员。他们太沉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太酷,太清高。复旦大学的学院经历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在复旦方圆1公里的区域里,他们是最放松的。而出了这个地域,我总觉得他们有点紧张。但谢立治是个例外,他频繁参加各种课程,以接触到更多的女孩子,他乐此不疲。
“布拉格之春”与戏剧的关系也该讲一讲。小戴和谢立治都是麦田剧社的成员,这个短命的新生代复旦剧社在他们手里诞生,也在他们手里毁掉。搞“布拉格之春”,似乎是复旦戏剧界一件强强联手的高兴事。也许乐队本身并不能归进上海地下乐队的大事记里,但绝对应该收编进复旦戏剧史。“布拉格之春”呈现出来的似乎是戏剧的音乐。
谢立治一定要我写清楚“布拉格之春”的风格是迷幻+噪音。似乎这样才显得出他们的先锋与出世。“布拉格之春”的音乐确实很“出世”。凡是看过乐队演出的人,都是摇着头出来的。可不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太high,而叫人兴奋得摇头晃脑,相反他们的音乐实在没劲,太没气氛。可他们不管,自个儿在台上一个劲地软磨硬泡,折腾个半小时,便灰溜溜地下来了。可小戴却满脸堆着笑,说:“我们今天又激怒了观众。”接着耳边就能响起谢立治一串猥琐的笑声。这还不算,排练的时侯,小戴和谢立治创造了连续演奏70分钟迷幻噪音的最高纪录。而尹达写歌词,也总是拿出他写诗歌的劲道,“厕所”什么的,写了一堆。但有一点我相信,在音乐里,“布拉格之春”是自足的。他们更像支训练心理承受能力的研究小组,在冗长的音乐篇章里,配合环境、配合心境,在音乐上实践某种微妙的变化。(柳生) 布拉格之春--校园是根据地
用网上我们乐队的介绍说一下风格,通过别人的眼睛,算是避嫌。"在布拉格之春的音乐中你找不到任何乐队的影子,也正是丰富与简约,旋律与噪音的同时存在造就了一种阴暗、冰冷、压迫却又使人迷失于其中的音乐。乐队还是被外界更多认为是一支实验团体。"
写文章写到自己的乐队有时候是件很尴尬的事,而且说谁谁谁的音乐风格在现在是一个讨骂的事,因为好像每个乐队都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和卓尔不群。我们乐队从没有标榜自己,但做东西的实验性在上海确实有点另类。
不过,这篇文章用不着对音乐做过多的评价,只是交代一下我们几个成员的生活状态。 我们乐队是我目前了解到的可能是上海物质生活最充裕的一个乐队,因为乐队的几个成员都是从前或现在的复旦的学生。走出去,找一份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工作还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和我们相似的大概只有"惊弓之鸟",他们是一支从华东理工出来的乐队。 现在我在一家报社做记者;戴征骏在一个很大的日本的广告公司;谢立治去年辞去了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目前和还在读研究生的张安定一块全力备战GRE;储智勇最小,不过明年也该毕业了,相信工作性质会和我差不多,因为他读的是正经的新闻系。
我们乐队现在的阵容是由三支乐队拼凑起来的。我和张安定进校没多久就认识了,因为当时住的宿舍都在一层,彼此兴致相投,平常就在一起玩、喝酒、听音乐,有一年 Kurt Cobain祭日的时候,我们还一块连续出了三期海报寄托哀思。
张安定最早去学的吉他,当时是从师刘海深--当时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演示会上能时不时用牙齿咬琴,把我们都震呆了,不过现在想最没意思的就是这种炫技的Solo。他现在在复旦旁边开了一家很小的琴馆,主要还是靠教学生维持生计,已经很长时间没了他们要演出的消息。
大概是98年初的时候,我、张安定和另外两个朋友泡饭吃了半年,终于攒足了买电吉他和电贝斯的钱,又搞了一个小鼓,四个人算是凑成了一个乐队。后来一个人退出了,剩下我们3个,还是充满了激情。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学校的一个小篮球场上,演的 NIRVANA的歌,当时我还在弹贝斯,没有鼓,找了当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用鼓机做。现在这个朋友在华师大后门开了一家琴行,用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叫"李奇琴行"。很久没联系了,主要是复旦离华师大太远。
最初的时候,歌都是我用木琴先写出来,然后乐队再排,但终究因为技术和能力有限,那些歌现在看太稚嫩。过了几个月,原来做主唱的朋友也离开了乐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只能没事的时候坐在校园里的草坪上唱唱民谣。 后来认识戴征骏和谢立治,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学校了做戏剧,他们是"麦田"的人,我是"燕园"的人。他们也是刚刚散了乐队,也剩下两个人。所以,四个人凑成了现在的"布拉格之春",我把贝斯交给了谢立治,当上了主唱。
四人阵容开始后,乐队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大家虽然在音乐上各有各的想法,但平时排练是还是统一在类似Joy Division的"后朋克"和Pink Floyd的"迷幻摇滚"的基调上。乐队就是这样,不同观点只能在统一风格的基础上保留。要不,几个人在一起整天吵架,音乐没法做。
认识现在的贝斯储志勇,也是因为住在一个楼里,我和张安定在楼道里唱歌,他常下来看。后来我和张安定找他在我排的戏里做演员,又一块做了戏的音乐,大家熟络起来。后来他们原来?quot;朋克"的乐队"地洞"解散后,进了我们乐队,把谢立治解放出来做另外一把吉他,我们做的东西更自由也更丰富。
后来的演出还是挺多的。因为乐队后来做的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大家习惯互相看对方的暗示,所以形成的演出风格比较奇怪,除了我这个唱歌的人,大家基本上都背对观众。后来我也干脆唱着唱着也转过去。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排练了,大家都太忙,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阵容还能维持多久。
單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