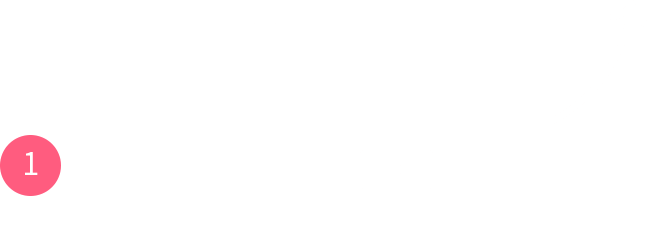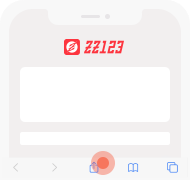英文名:Fou Ts'ong
国籍:英国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34年3月10日
逝世日期:2020年12月28日
职业:钢琴家
主要成就:《玛祖卡》演奏最优奖
父亲:傅雷
傅聪(1934年3月10日-2020年12月28日),生于上海,8岁半开始学习钢琴,9岁师从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1954年赴波兰留学。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1959年起为了艺术背井离乡,轰动一时,此后浪迹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据央视新闻援引奥地利音乐频道报道:2020年12月28日,傅聪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傅雷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傅雷对多种中西艺术、文化的渊博学识,独到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真理的赤诚追求,直接、长期、深远地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
三四岁时的傅聪,已能感受到音乐的强大吸引力,显露出对音乐不寻常的热爱。七岁半开始学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的梅帕器(Mario Paci)为师。梅帕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其门下受教三年。
傅聪于1951年夏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Ada Bronstein)夫人为师。傅聪刻苦用功,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在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不禁泪下。
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为薄弱的一位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与前两名相近的分数获第三名,还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该届比赛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经赛后傅聪继续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宝贵的专业钢琴家的舞台经验。
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已经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同年的12月傅聪再度返国。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已经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讲过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斯卡蒂等人的作品。还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并兼任指挥;还专门指导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小组的训练。他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博得广大师生及音乐爱好者的赞扬和尊敬。
纯真的初恋在长相思中失却:幸运与痛苦常常是一对形影相随的孪生子。20岁的傅聪,是令人羡慕以至嫉妒不已的幸运儿。连音乐学院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的他,硬是凭着自聘导师指点,靠着汗湿琴凳苦苦练习拼出来的;何况,在1954年出国留学如同稀有元素,只有尖子中的尖子才有这样的希望。他,居然被文化部选中,派往波兰深造。
当时,他正处初恋之中。离别,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思念。他回首往事时,曾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对于初恋的感情:“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青梅竹马,那种纯真的爱,永远给他留下“美丽的回忆”。
傅雷知道儿子在波兰刻苦练琴之余,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确实,知子莫若父。而傅雷正是以自己在爱情上的深刻教训,为儿子指点迷津。傅雷如此告诫儿子:“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奈何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的。”
不久,命运的旋律急转直下,父子俩同遭厄运,无暇再讨论恋爱观问题了。傅雷,蒙受历史的误会,被错划为“右派”;傅聪,怕受父亲的牵连,从波兰出走英国,与家中断绝音信。
有国难回。傅聪只好从此侨居英国伦敦,以琴艺谋生。“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他的初恋也就此告吹。失去了祖国,失去了家书,失去了恋人,傅聪陷入深深的孤寂之中。
幸亏,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的关怀,让傅雷继续与傅聪保持通信。傅聪从家书中得到慰藉,略解相思相忆之渴。
与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之女结为秦晋之好:以世界作为舞台,傅聪“跑码头”,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登台献艺。他结识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并常同台演出。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的琴声,使傅聪倾倒。他的坦率、幽默和高深的音乐修养,使他们结下忘年交。
同时,傅聪也跟这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的家庭,有了不寻常的关系。他,爱上了梅纽因前妻诺拉的女儿弥拉。
在来到伦敦1年零8个月时,傅聪在家书中向父母透露了喜讯,顿时使傅雷夫妇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
傅雷,这位充满父爱、对儿子关怀备至的翻译家,放下手头的笔耕,给傅聪写去长信,告诉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
“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
三个多月后,26岁的傅聪和21岁的弥拉举行婚礼。
小两口最初的共同生活是甜蜜的。弥拉是一位阅世不深、单纯天真的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躁。傅聪辛勤地练琴,忙于演出,往往使她感到孤独。
婚后三年多,弥拉有喜了。孩子尚未出世,傅雷便已给孩子取好名字——生男孩叫凌霄,生女孩叫凌云。凌霄是一种艳丽的黄花,傅雷非常喜爱。傅雷夫人则忙着给未来的小孙子(小孙女)织毛线衣。
一个中西混血儿出世了。小家伙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
傅雷夫妇盼望着有朝一日与未曾谋面的儿媳妇、小孙子骨肉团聚。他们常常梦见弥拉、凌霄忽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家中。
“文革”撕碎了一切梦。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了这个世界,团聚之梦化为泡影。
两个多月后,傅聪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噩耗,天旋地转,热泪纵横。
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婚恋:十多年后,傅聪和弥拉的家庭破裂了。用傅聪的话来说,缘由是“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过一次草率婚姻。他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傅聪的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3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3个月,短暂的婚姻。” 仓促的结合,导致迅速的离异。 他,又成了形单影只的独行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而行。 终于,一位中国女性的琴声,引起他心中的共鸣。 她,卓一龙,一位出生在“琴岛”——厦门鼓浪屿的女钢琴家。她是一位从小便在琴声中长大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当地富商,曾任亚细亚石油公司经理代理人。母亲叫周默士。后来她随父母去香港,仍不断练琴。她终于获得了奖学金,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深造。琴为媒,同为钢琴家,同为炎黄子孙,傅聪和卓一龙相爱了。他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1974年,她和傅聪有了第二个儿子。傅聪无法再请父亲为儿子取名,就用当年父亲“备用”的另一个名字——凌云,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大名。
傅聪四口之家,生活在伦敦。1979年,在祖国挣脱“文革”噩梦之后,傅聪回到了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1982年,傅聪带着夫人卓一龙、次子凌云从英国来到北京。岁月飞逝。如今,傅聪年近花甲,和卓一龙一起住在伦敦一幢三层小楼里。他在弹琴之余,喜欢看网球。他为两个儿子的成长感到欣喜。遗憾的是,在琴声中长大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
父亲:(“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烦,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晨六七点就醒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真的,你那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生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摘编自《傅雷家书》)
爸爸这封信里说的事我还记得。那还是我在波兰留学的时候,第一次回国,大概是1956年吧!我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呵!整晚谈的是各种各样的题材,音乐上的,哲学上的,真是谈不完!
我在13岁到17岁之间有3年多的浪子生涯,一个人呆在昆明,念云南大学时我才15岁。当时我当然没念什么书,整天在搞什么学生运动啊、打桥牌啊、谈恋爱啊···可以说我17岁回到上海的时候比一般17岁的孩子要早熟,那时我才真的下决心要学音乐。那时我和父亲之间已经象朋友 一样了!后来出国几年,自信心也多一些,56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他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他对我说的很多话都会肃然起敬,我讲的音乐上的道理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他来说,这不是父亲和儿子的问题,而是学问的问题,在学问面前他是绝对谦虚的!
离开上海时父亲的临别赠言其实我从小就听他说过:“做人,才做艺术家,才做音乐家,才做钢琴家。”其实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天然的事情。我从小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念——活下来是为了什么?我追求的又是什么? 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且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做人的基本的精神价值。这个面很广,不一定是要在琴上练的,而是要思考。我的这种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一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事实上《家书》里说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现在一想起它,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朴素,很简单,很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他的内心挣扎,他与社会不能和谐,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还有他本人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出国前我去北京的时候,他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信给我,象写忏悔录似的,写大自然怎么样冰封,小草怎么样在严寒折磨之下长出来,应该感谢上苍。可惜那些信都没有了,假如还在的话,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我亲眼目睹我父亲受苦受难,还有他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这使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早熟了。那是因为我很早就看到人类灵魂的两极。人的灵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圣、又恐怖又美的东西啊!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里看到了,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悲剧我也看到了——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说我家里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家里那种大波大浪我是从小跟它一起成长的。这些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这些经历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我当年真正在父亲身边的时间还很短,真正学到的东西其实很少,大部分东西都是我后来才看的。所以我回国到音乐学院讲学的时候,在台下经常有教授抿着嘴在笑,因为我念白字,我并没有学过这个字怎么念,我只是通过看书来潜移默化。是父亲开了一个头,给我指引了一条路,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他也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知识本身是有限的,可追求是无限的,有追求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我没有做到,这是非常惭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他比我严谨得多!我想我做学问也够严谨的,可在一般生活小节上他也极严谨,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有条有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象有点矛盾,你从我父亲的文章也能看出来,有一股火一样的热情和气势,可他写东西的逻辑又是那样严谨。这一点我觉得他跟肖邦很象!肖邦也是每一样东西都考究得不得了,严格得不得了,没有哪个作曲家象他那样严谨。可是正象列宁(此处有误,应是舒曼——作者注)说的,肖邦是埋在花丛里的大炮,他蕴藏的爆炸性是很大的,只是他把它弄得那么美,那么细致,你不去仔细挖掘的话,就会被外表的东西迷住,不知道那里头有很深很深的东西。我总是后悔没有老早就改行,因为弹钢琴这个职业磨在钢琴上的时间太多了!音乐这东西应该是凭感受、凭悟性的,我就无时无刻不在动心思。我并不要太艺术化的生活,我平时要花那么多时间练琴,把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琴上面了!我父亲做人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他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那他就会洋洋洒洒象写一本书一样回一封信。我就做不到这一点,能打个电话就不错了,要我回封信就太辛苦了!因为我几十年在国外,尤其是父母过世之后,我基本上不再写什么文字了!多苦啊,写一封信要花几天,那我也不用练琴了,得放弃了!那样的话,真是愧对江东父老!所以在《傅雷家书》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为我不愿意发表出来,我觉得那些东西太幼稚了!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虽然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距离。
我爱音乐,可弹琴是苦差事。小时候我也爱玩——也难怪父亲要生气,我要是他,发现儿子这么干我一样会生气:琴上放着谱子,我有本事同时看《水浒》,样子好象在弹琴,手指好象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怎么样怎么样。爸爸的耳朵很灵,听着不大对,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大喝一声,真的象李逵大喝一声一样!也难怪,小时候喜欢是一回事,我想小孩子很少有自己愿意下苦功的!其实凭良心说,我小时候学钢琴底子很差很差,真正弹琴只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对父亲反抗,家里闹得不可开交,简直没办法弹了!不光是去昆明的3年,以前那些年都那样!所以我的基础很差很差!我真正花工夫是17岁时第一次回上海,18岁就第一次公演,说起来这真是“天方夜谭”!这是全世界学音乐的人都觉得不可置信的事情。一两年之内就去参加肖邦比赛,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荒唐,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过我对音乐的感觉非常强烈,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刚刚开始学琴的时候,教我的老师和我爸爸都说:“孺子可教也!”因为小时候虽然什么也不会,但我弹琴时非常自得其乐,我觉得我到了一个极乐世界,在这一点上,我想恐怕很多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都从来没有达到过!这跟他们的技术、修养都没关系,这只是上天给我事业的一种特殊的眷顾!
今人·古人·造化:记得父亲那时候给我寄黄宾虹的《画论》,跟我说这《画论》里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对音乐也一样通用。我以前也有所感,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看黄宾虹的画,更悟到以前有所悟而没有深刻悟到的一些东西。
我在各国讲学的时候经常举个例子,那就是黄宾虹说的“师古人,师造化,师古人不如师造化”。最近,就是来长沙这几天,我又翻了一下,发现他说得更妙了:“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然后他拿庄生化蝴蝶作一个比喻,说“师今人”就好象是做“虫”的那个阶段,“师古人”就是变成“蛹”那个阶段,师造化就是“飞了”,也就是“化”了!我觉得这个道理太深刻了!为什么我说这个重要呢?现代科技发达了,CD到处都是,学音乐的人很容易就可以听到很多“今人”的演奏,也可以听到很多“古人”也就是上一代大师的演奏,可是真正音乐的奥妙这些所谓的“今人”和“古人”也是要从“造化”中去体会出来的!为什么说“造化”这两个字特别妙呢?因为音乐比任何其它艺术都有更加自由的流动性和伸缩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最高的艺术。“造化”这个词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没办法翻译,它是中国文化里才有的概念。这个“化”字很妙,它可能有道家的“道”的含义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是通的,西方人是没办法来解释的。音乐太妙了,伟大的作曲家写的作品完成后还会不断地发展,它会越来越伟大越深刻越无穷无尽,所以“造化”跟自然一样生生不息,不断复活、再生、演变。现代人基本上“师今人”,在黄宾虹的说法里是很低级的,“师古人”已经好一些了,因为“古人”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还是比现代的精神境界要高很多,所以他们得到的“造化”后面的“道”一般来说要比“今人”高出很多。真正的“造化”是在作品本身。我讲学并不是把我懂的东西教给我的学生。说到这里又得提到我的父亲,他给我作了一个活的榜样。学问并不是我有,学问也不是我爸爸有,学问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几千年的积累,是人类的共同智慧,可是,怎样追求这个学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学问”了。我教学生时觉得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学生,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个古人,只不过我还没有作古而已!我给学生指出的不过是我所看到的那个“造化”里头的“造化”,其实真正的“造化”无时无刻不在“造化”本身。我给一帮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是一起去追求、研究“造化”里边的奥秘,当然有时候他们启发我,有时候我启发他们,大家会有一种灵感。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要有这种追求的愿望,有这种“饥渴”。
我说应该效仿“古人”,也就是因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在成就上没有超过我说的这些“古人”。其实在欧洲就有很多大音乐家对现代音乐的很多东西也不看好,象一位“古人”、在1950年左右过世的德国大钢琴家施纳勃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一辈子只研究、只弹我永远也弹不好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精神境界是如此之高,艺术水准是如此完美,没有任何演奏可以达到作品本身具备的“高”和“美”。可是象那样的音乐正是他一辈子要弹的。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成为机器的奴隶、商业化的奴隶,追求精神价值的我们已经成为了古董,真的是古董!莫札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德彪西···这些人的精神境界对我来说就象咱们中国的老庄、杜甫、李白一样地高。那种高度,现在真是没有人能够企及的!
莫扎特:说来我根本没有资格评价莫札特!
以前我说过,贾宝玉加孙悟空,就是莫札特。为什么这么说?第一,莫札特绝对是赤子之心,在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博爱,有一种大慈大悲,这一点和贾宝玉是一样的。莫札特是歌剧作曲家里与众不同、绝无仅有的一个,他洞察人间万象,对人的理解到了最细微之处。就象贾宝玉,对《红楼梦》里那么多人物,他都理解,他永远不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他有时候也有反抗,跟莫札特一样。莫札特曾经反抗一位主教,非常激烈,他非常有傲气,但他对每个人的心都有那么深切的体贴。他在歌剧里写角色,就象《红楼梦》一样,每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你听一句词就知道是谁唱的和说的。甚至于在《后宫诱逃》中,在苏丹王宫前有一个又懒又胖又蠢的守门人,唱着咏叹调,在那儿怨天怨地。虽然只是这样一个角色,可是你听他那歌词里的悲哀,你会觉得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真正伟大的艺术,就象王国维讲的,“后主词,赤子之心者也”!真是血泪铸成的!还有王国维说的另一句话人们往往忽略了:“象哈姆雷特和释迦牟尼一样,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感。”所以说,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不是一个人的长恨而已啊!所以,在莫札特的音乐里,即使是最平凡的人物,他的音乐也是美得不得了,同时音乐本身又有一种永恒的深沉,一种无穷无尽的意义和感情。还有,我为什么说他是孙悟空呢?他就是千变万化,因为他的天才是超人的,他能上天入地,就象孙悟空一样,拔一根毛就可以变一样东西。你给莫札特一个主题他就能编,要怎么编就怎么编,而且马上就编。这个本领就是孙悟空的本领了!而且他也非常之俏皮,他的幽默感不是一般的说说幽默话,他的幽默充满了温柔,而且有一种童真。中国人其实就是“莫札特”,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就跟莫札特有很多地方相似,而且能入能出。莫札特的音乐里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尤其是他的歌剧:他是在做戏,你能感觉到这是戏,但是你又发现这里面的感觉是真实的,这似乎不是做戏,可是事实上它又绝对是在做戏。这跟中国的戏剧也有相同的地方。中国的戏剧很明显是在做戏,但是它就是有个艺术的高度,它能入能出,在“入”的同时也“出”了,它在外头观察。所以,欧洲有些人就说莫札特象音乐里头的莎士比亚。莫札特的音乐是那么地亲切,那么地平易近人,可是它里头有无限的想象,充满了诗意。所以我说莫札特是“中国的”,他跟中国人的文化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应该比任何民族更懂得莫札特! DOWNBEAT
肖邦:演绎肖邦我说不上是权威,我不过是他一个忠诚的追随者。“熟读后主词”,就基本上是肖邦的精神。肖邦的音乐最主要的就是“故国之情”,还深一些的,是一种无限的惋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穷尽的怀念!这种无穷尽的怀念不光是对故土的怀念,那种感情深入在他的音乐里,到处都是一个“情”字啊!这是讲肖邦音乐的那种境界,他其实是一个根植得很深的音乐家。我要是能够再活一次的话,也要象黄宾虹画画一直追求到唐宋以前一样,从那个根子里打基础,再慢慢地“画”出去。黄宾虹活到90岁才到那个境界。我这辈子弹钢琴本就是半路出家,基础很差,要我现在重新从巴赫再到巴赫以前是不可能了!我平常喜欢听的音乐中钢琴的最少,基本上是跟钢琴没关系的。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是戴留斯,他就从来不写一个钢琴作品(这个说法好象有误?至少戴留斯还有一首钢琴协奏曲——作者注)。因为我喜欢的是音乐,音乐是一个很巨大的无边无限的世界。肖邦古典的根是很深的。他的音乐和声非常丰富,同时对位复调的程度非常高,不象巴赫的,一听就是对位,他的不是,可是又无处不在。可以说,他的音乐里面包含着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里线条的艺术,尤其是黄宾虹山水画里的艺术,有那种化境、自由自在的线条···一般人弹肖邦,只晓得听旋律。肖邦的旋律是很美,可是在旋律美之外人们往往忽略掉了它其它声部的旋律。他的音乐是上头有个美丽线条在那儿,下头还有几个美丽线条无孔不入,有很多的表现。除此之外,肖邦音乐还有和声的美。不象一般的弹钢琴,右手是旋律的话,左手就是伴奏,肖邦的音乐里没有伴奏,里头都是音乐,都有丰富的内容。为什么人们都说肖邦是“钢琴诗人”?他的音乐真是最接近于诗!人们都说肖邦一定要歌唱,其实在歌唱之前,肖邦他一定要舞蹈,他的音乐全是从民间舞蹈出来的,每一句都是这样!即使是他的叙事曲,里面都有玛祖卡和华尔兹的影子。他的协奏曲也是这样,比如说第一协奏曲,第一乐章后面有波兰舞曲的影子,不仅如此,开始那个乐队的部分还是玛祖卡呢!很多人包括西方的音乐家都不知道!我说透之后,他们觉得很惊讶,但是仔细一分析,又觉得有道理!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肖邦要说话!肖邦的音乐跟诗那么接近,好象他在跟你说话。有一首他的E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次接触它时,最后那一段我就感觉真是“泪眼望花花不语,乱红飞过千秋曲”(此处引用有误,应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原句出自欧阳修词《蝶恋花》——作者注)!“乱红”颜色的感觉真实极了!每次我弹这个曲子就真是那个感觉——泪眼望花花不语!肖邦的音乐那个感人啊!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在对你说话!肖邦真的跟诗是最接近的!
我一说起来就好象每一个作曲家都跟中国的诗有关系,比如说陶渊明就很象舒伯特,贝多芬和巴赫就少一些,但是贝多芬在“苦”这个程度上跟杜甫有点相象。肖邦的音乐真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接近很接近,所以这次波兰肖邦钢琴比赛,最让波兰人震撼的并不是某个人得奖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代表团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认为这些中国人基本上都有那种肖邦的感觉。对肖邦有感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全世界都很少,因为肖邦那种诗一般的语言和他那种深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缺少,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执着真是很少很少!
中西艺术:我曾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在很多方面我父亲都是一个先知者。他说中国音乐的发展要从语言里去发展,事实上所有国家的音乐都跟它的语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俄罗斯音乐如莫索尔斯基的歌剧就是从他们俄罗斯的语言里挖掘出来的,他的音乐语言跟他们民族的语言息息相关!德彪西的音乐跟法国的语言相关,舒伯特的音乐跟德语相关。至于中国音乐,在音诗方面,赵元任也作过很多尝试,这条路至少是发展中国音乐很重要的一条路,我觉得他完全是对的!很妙的是,很多年以后,我给学生讲一首德彪西的练习曲,其中一段的抑扬顿挫、起伏迭宕跟纳兰性德的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常常讲德彪西是“中国”音乐家。这世界真是奇妙,德彪西这样一个完全从另外一个文化出来的人,会这样完美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就经常用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来诠释西方音乐,西方人对此很感兴趣,而且他们在我加以解释之后的感受都很强烈。
中国民族音乐在1979年以后是不一样的,开放了,对于音乐艺术也没有那么“教条”了!而从刚解放到1979年,中国基本不存在音乐,只有宣传口号,跟音乐毫无关系!以后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学派,有法国的梅西安这样的世界级现代作曲大师也有美国来的音乐家到中国来讲学。有一批年轻的中国作曲家现在在欧美,他们在做很多尝试。我觉得在这一批中国作曲家里,有很多是很有才气的。比如说谭盾吧,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放在京剧团里头,接触了许多中国过去的戏剧艺术、民间艺人,我觉得这太好了,对他来说,这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比起在学校里学对位、学作曲好得多!这才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土壤。可是有一个问题:学现代派也很容易走火入魔···音乐比其它东西更需要时间的考验。我想过一二十年我们回过头来看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音乐学校去学习,学习钢琴、 小提琴或者其它乐器,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成名成家的捷径,那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也许真能做到,这孩子天分很好,但是假如他追求的就是这些的话,他的价值就不是我认为的音乐艺术里面的价值,而是世俗观念里的价值,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价值。假如说学音乐是因为孩子真的很爱音乐,而且他有强烈的感性,还有他知道音乐是苦差事,愿意一辈子做音乐的奴隶,有献身的精神,那就是另外一说了!假如不具备对音乐那种“没有它就不能活”的爱,那还是不要学音乐,学电子、学医、学法律成功的机会都会大得多!学艺术一定要出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有“大爱之心”,然后要愿意一辈子不计成败地献身。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是这样的出发点,假如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即使孩子不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可是他有了一个精神世界让他可以在那儿神游,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学音乐本身是很好的,我父亲当年也并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显露出的那一点点悟性和音乐感就认为我能够靠它成名成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不过是觉得人文的东西都应该是通的。他从小在美术上、文学上、哲学上给我的那种教育绝对不亚于在音乐上的,甚至可以说比音乐上的更多一些。他让我学音乐就真是这样想的:假如有发展,就往这条路上走;没有的话,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构成我的人格修养、精神境界里一个很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他真是这么去看的!我觉得人们都应该这么去看,都应该喜欢艺术。黄宾虹说:“艺术可以救国。”真的是这样!艺术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精神价值现在真是太缺乏了,全世界都一样!
自我剖析:凭良心说,在钢琴上我花的精力最多,这并不是说我注定要成为一个钢琴家,而是因为我的根底不够。我小时候学琴学得很少,最关键性的那几年也就是13岁到17岁那几年,我根本没有机会去弹琴,17岁再开始也没有很好的先生,不象现在的一代,他们真是幸运得很,童子功好得不得了,基础打得很稳固。随着年龄一年一年增长,对我来讲,纯粹在技术上要征服钢琴这种东西真是花费了我太多的时间,所以真要说起来,我做钢琴家永远觉得难为情。这是就钢琴家纯粹机械性的这个方面来说。到我这样一个年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加倍甚至于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所以这几年我的手老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虽然现在我这手的条件不好,练起来更苦,可我还是坚持练琴。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可以每天练8到10小时。我手上这腱鞘炎这绷带可能就说明我的童子功不够,童子功好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么辛苦练琴了!从纯粹机械地弹钢琴的本事来说,所有钢琴比赛里的选手、所有音乐学院里的学生都比我强,真的是这样!可是讲到追求一种精神的境界,讲到声音的变化,讲到音乐里头“言之有物”,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练琴,在这方面他们好得很,他们倒是需要多读一点书,多看一点画,多思考!
我父亲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精神。”艺术里头的完美你要心里头有数。就象我前边说到施纳勃所说的,伟大的音乐你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你的演奏永远不可能象作品那样完美。对此你心里有数,可你还是孜孜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去追求这个东西,而且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也有一种无穷的乐趣,你每一分钟都会发现新东西,每一次你发现的东西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啊!每一次你又能看到多“一滴水”,你会高兴你又看到新东西!
说实在的,现在弹琴我觉得很累,真的很累!我真想还是帮助下一代,带个徒弟吧!我现在教课也教得多,一般是教大师班,不过我一般不教私人学生。“大师班”这个名称并不是说我认为我自己就是大师,它一般是上大课。我讲音乐并不是把我那点有限的知识教给我的学生,就象我爸爸,当年他也不是把他的知识教给我,而是启发我,让我动脑子,也就是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去思考。我讲学一般喜欢讲大课,我的目的是发掘音乐里面的奥秘,怎么样去表现这个奥秘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探求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这些年一直在看中国书,古书也好,现代书也好,我一直都在看,不断地看。我家里也有很多画,特别是黄宾虹的画。可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我的脑子里有中国的文化。怎么说呢?凭良心说,我念的中国书是非常有限的。前几年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小时候爸爸教我的第一课讲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是我一生的写照!对此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学,经常不断地复习,再继续研究。我在国外是这样翻译它,而且我对这种翻译相当满意:“LEARN AND CONSTANTLY RESTUDY,ISN’T THAT PLEASURE?FRIENDS COME FROM FAR AWAY,ISN’T IT JOY?”“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我来说就是SHARE,我跟朋友分享我的“学”。凭良心说,我基本上是这么做的,至少我是往这条路上走的。中国文化本就是我的一部分,没有这个就不是我了!文化和我是完全一体的!
其实,我···我很怕回国!我每次回国心里都是很疼的,有很多让我非常愤怒的东西,也有很多使我非常高兴的东西和使我非常惋惜的东西。这种感情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里翻腾,当然,作为艺术家,我不能把这么具体的东西放到艺术里面去,而是应该升华到另外一个程度。我们祖国的文化实在是太伟大了,它包含的力量太大了,我比一般人的感受可能要强烈得多!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在感情上不能承受这种文化对我内心的冲击。还记得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我曾经到成都,去武侯祠,看到了岳飞(此处有误,应为诸葛亮——作者注)写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要掉眼泪!那个感人啊!那种人格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感人! 有人注意到我练琴时嘴也在唱,其实这是我的缺点!当然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象卡萨尔斯,他是公认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你听他的唱片,嘴里也是哇啊哇地在那哼哼,还有加拿大的格兰·古尔德,也是唱的声音比琴声还响。可是我得承认这是我的缺点,我不能控制自己。就象我爸爸信里说的,音乐一定要能入能出。我练琴时“入”是入了,可是没有“出”啊!假如不发出那种声音,我就能更清楚地听见我弹的声音,我就能控制它,能够做到接近于“能入能出”。我就是没有能够做到。反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还能少唱出点声音,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集中”,所有人都在听我,我也会更加清醒地听到我自己弹的声音。为什么说莫札特“能入能出”?他的音乐是在做戏,同时他又在看戏。这也就是中国戏剧的高妙之处,这也就是跟莎士比亚相通的地方!
评价:傅聪在国际乐坛受尊敬的程度,远远胜于其他大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是美国《时代周刊》以及许多重要音乐杂志的封面人物;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钢琴家仍常常向他求教;世界重要的国际钢琴大赛,他是理所当然的评委。傅聪说:“只要我多活一天,就越发现音乐的高深。我觉得,60岁以后才真正懂得音乐!”
荣誉记录: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奖
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钢琴比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