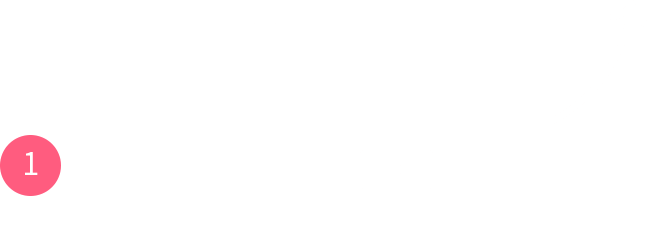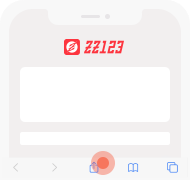Кино
前苏联摇滚之父。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生的第三代韩裔移民,摇滚乐手兼电影演员。代表作:歌曲《血液型》、《变化》、《最后的英雄》、《星》;电影《针》、《阿萨》。
在中国,崔健(朝鲜族)被称为中国的摇滚之父。在前苏联,也有一位姓崔,民族也和崔健一样的摇滚之父——叫维克多-崔。6月21日是前苏联最后的英雄维克多-崔的生日,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特撰写此文。
这世界上有一些已经去世了但并没有消失的人,在人类的历史中一同呼吸,时常被记起的那些人,我们称他们为英雄。在已经解体的前苏联,有一个被称为最后的英雄的人。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伟大的思想家或是宗教人,更不是军功卓越的军人,他仅仅只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已。为什么俄罗斯的年轻人把他称之为最后的英雄?为什么在阿尔巴特2号他的追悼壁(又名痛哭之壁)前面至今还在响彻他的歌曲?为什么人们继续在书写怀念他的悼文?为什么他的墓碑前面的鲜花每天都是新鲜的?
维克多-崔1962年6月21日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基乌尔达,父亲是韩裔崔东烈、母亲是乌克兰出生的瓦莲齐娜-巴锡尔耶夫娜。在他5岁时,全家搬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日后在他去世后,从前苏联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就他的国籍问题进行过争论。最后这场争论以国籍为俄罗斯,但标明出生地为哈萨克斯坦终结。不过至今哈萨克斯坦人很骄傲的认为维克多-崔就是哈萨克斯坦人,而且把他列为代表哈萨克斯坦的13名伟人之一。
对画画有着天赋的维克多-崔考上了谢洛夫美术学校。除了画画,他在文学和音乐方面更显示出过人的天赋,15岁就开始自己作词作曲。1974年在学校里和马克西姆·巴徐科夫组织了名叫“第六病室”的摇滚乐队。但摇滚在当时的苏联体制下是被视为反国家歌曲,维克多-崔也因为演奏摇滚乐的理由被学校勒令退学。被美术学校勒令退学后,维克多-崔考上列宁格勒市立第61技术专门学校,学习木刻。在学校里遇到阿列塞-鲁宾、奥列格-巴利斯基等人,1981年组织了名叫 “加林和双曲线”(Гарин и Гиперболоиды)的乐队。在这个时期,遇到初恋情人阿鲁卡基娜,尝到了爱情带来的酸甜苦辣滋味,《8年级女学生》就是为阿鲁卡基娜所作。
在偶然的机会下,维克多-崔遇到俄罗斯当代最出色的摇滚乐队“阿科瓦里姆(Akvarium)”的主唱鲍里斯-格列本许科夫。在鲍里斯的影响下加盟摇滚乐队协会,通过与其他著名摇滚乐队的交流,更加丰富了自己的音乐元素。而对维克多-崔慧眼相识的鲍里斯不惜屈尊出任了维克多-崔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当时因为奥列格-巴利斯基退出,维克多-崔组成了崭新的乐队,即成为旧苏联历史上最伟大摇滚乐队的KINO(意为电影)。在第一张专辑推出一个月之前,维克多-崔开始和马莲娜同居,马莲娜也出任了初期KINO的经纪人。和马莲娜的同居也有很多波折,最大的理由是马莲娜的父母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没有正当收入,又是黑头发黄皮肤的韩裔小伙子。在艰苦的情况下终于完成录音,1982年KINO的第一张专辑《KINO45》出世。后面的45据说是因为演奏时间共45分钟,维克多-崔即兴打上去的。不过第一张专辑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维克多-崔的生活依旧拮据。因为搞摇滚,维克多-崔未能正式毕业第61技术专门学校,以结业的形式走出校门。不过如今市立第61技术专门学校走廊正面,挂着最值得骄傲的毕业生维克多-崔的照片,整个学校里的装饰几乎都是维克多-崔的作品。
1982年,维克多-崔和KINO发表了第二张正式大碟《不著名的歌曲们》,这张专辑中有维克多-崔早期成名曲之一的“最后的英雄”。
1983年KINO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摇滚乐队大奖赛,不过因为主办方不可理解的判分,KINO遭到惨败。因为此事,KINO内部出现分裂,阿列塞-鲁宾退出了乐队。不过他的磨难并没有结束。1984年和马莲娜正式结婚后,维克多-崔肩负一家之主的重担,除了摇滚以外,还得干活养家。千辛万苦之下找到的是坎察特卡锅炉室的火炉工工作,在这里维克多-崔边干活边作歌,完成了第四张专辑《坎察特卡的队长》。在他死后,这个小小的锅炉室成为了象征俄罗斯自由和抵抗的圣地。(注:第三张专辑《KINO46》,其实是第四张专辑的DEMO版本)
1984年维克多-崔和KINO参加第二届摇滚乐队大奖赛,一举获得大奖,1985年再次蝉联这个荣誉。1985年还发生了维克多-崔认为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儿子阿列山德罗-崔来到这个世界上。
虽然已经推出了四张专辑,不过维克多-崔依旧还是没有被大众认可的地下音乐人。遭受着贫穷的折磨,1985年KINO倾尽浑身之力完成了专辑《Noch》,但因为和录音师的摩擦未能在当年出版,转而推出了第五张专辑《这不是爱情》。市场对这张专辑的反应,和前几张一样,还是冷冷淡淡。
1986年,本该作为第五张专辑的《Noch》终于出版。因为连连遭遇失败,谁都没有对这张专辑抱以希望。不过这张专辑出人意料的成为市场的新宠,推出两个月售出50万张,再过几个月销量达到了惊人的200万张。
维克多-崔的歌曲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除了简明有力的曲风以外,反映了当时年轻人心声的歌词更是主要原因,这一点上维克多-崔和崔健有极为相似的地方。“血液型”是维克多-崔最经典的代表曲,看一看歌词:“温柔的安乐窝,不过街道在等待我们的脚步 / 军靴上面如星光的尘埃…… / 舒适的沙发、格子纹络的沙发套、没有按时扣动的扳机 / 阳光照耀的日子只是在灿烂的睡梦中 / 虽然有付出代价的手段,但我不希望廉价的胜利 / 谁的胸膛我也不想践踏 / 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我只是希望和你留在一起 / 不过天上高高的星星召唤我上路 / 我的袖口上记着血液型 / 我的袖口上有我的军号 / 为冲向战场的我祈祷吧,为我祈祷吧 / 不要让我留在原野上 / 不要让我躺在原野上 / 祈祷我的胜利,为我的胜利祈祷吧”
年轻人马上能读解了这个歌词中隐藏的意义,即“这个世界就是你们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得由你们自己来改变。战斗吧!不要躺在荒凉的原野上,尽情战斗吧!我会和你在一起,祈祷着战斗的胜利和幸运……”家家传出了这首歌,年轻人们在大街上高声唱起了这首歌,KINO热潮如旋风般瞬间占领了苏联全国。
有一个插曲能反应他们当时的人气。KINO受邀去切利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进行演出,坐了长长的时间到达切利亚宾斯克的KINO一行,被对他们持有反感的车站工作人员带到警察局。警察局命令他们马上回到列宁格勒,并软禁了他们。无可奈何的KINO一行却从窗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情景,手持蜡烛的年轻人们正包围着警察局。这些年轻人是邀请KINO的大学生,听到KINO被软禁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进行蜡烛示威。“把KINO还给我们!”“我们要维克多-崔!”警察局长面对这样声势浩大的示威,担心会演变成暴动,只好允许KINO的公演。在蜡烛示威队的护送下,KINO来到大学,过不多久操场上想起了维克多-崔和学生们齐声喊唱的“血液型”歌声。为了维克多-崔,苏联年轻人们勇敢的挑战警察局这个国家权力机构,并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变化就这样在开始。
1989年推出的第八张专辑《最后的英雄》中,收录着维克多-崔两大代表曲之一的“变化”(另一曲为“血液型”)。这首歌的歌词十分简明的反应了当时苏联年轻人对自由的意志:代替热气的绿色的玻璃 / 待其火焰的袅袅烟火 / 月历中的一天就这样消亡 / 红色的太阳燃尽 / 一天也随着燃尽 / 燃烧的都市里落下夜色 / 变化!我们的心脏在要求 / 变化!我们的眼睛在要求 / 在我们的笑容和我们的眼泪中 / 还有我们静脉的脉搏里 / 变化!我们等待变化
同一年维克多-崔拿出了第九张专辑《名叫太阳的星星》,这张专辑在俄罗斯卖出500万张,不过考虑到当时盗版猖獗的情况,可以说最少卖出了2000万张。1990年6月24日,旧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在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发生,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为了KINO乐队的公演燃起。在和创下纪录的10多万观众一起,维克多-崔唱起了“血液型”,尤其是唱最后一曲“变化”的时候,整个体育场因为歌声在颤动。结束最后一曲后,维克多-崔想歌迷摇手致意,说了最后一句话。“过不多久的夏天,新专辑就出来了,到时候再见。”
不过,维克多-崔未能遵守这个诺言。因为一个月后,维克多-崔因为交通事故,离开了人世。
“我们是率先成熟的果子,死神会率先扑向我们。”——维克多-崔
1990年8月,维克多-崔接到了让他兴奋异常的消息,爷爷的国家韩国向他发出了演出邀请。“就是推掉其它演出,韩国我一定要去”,接到邀请后的维克多-崔兴奋的向周围人说。因为韩国是维克多-崔一直向往的地方,那里有着他的根。
1990年8月,维克多-崔到拉脱维亚首都利加拍摄MTV并抽空度假。8月15日,钓完鱼开着车回到宾馆的路上,对面开来的大巴从正面全力冲向他的小轿车,把他的轿车往后撞退了10多米,28岁的天才当场死亡。
维克多-崔的死亡充满着重重迷雾,因为当局对事故的调查极为匆匆,肇事司机没几天就被释放,然后失去行踪,以至人们猜测这是KGB的所为。其实维克多-崔早已是当时苏联政府的眼中钉,他的歌曲尤为注重歌词。其尖锐的歌词破坏力极强,有些人甚至拿他的歌词和俄罗斯夭折天才诗人叶赛宁的诗相提并论。他的歌词,不,应该说是他的诗,具备了极强的感染力。他的以这个力量为基础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苏联年轻人心灵深处,使他成为了自由和抵抗的化身。他对年轻人的巨大影响,是保守派极度不愿看到的。
维克多-崔还被认为是影响戈尔巴乔夫的5人之一,戈尔巴乔夫曾约见维克多-崔,握着手说:“同志,为了perestroyka(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一起努力吧。”因为他的歌曲是perestroyka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是作为强硬保守派的KGB暗杀他的充分理由。
维克多-崔去世后的第二天,苏联所有激进派报纸都大大报道了他的死亡,但保守派的报纸则只字不提。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如此鲜明,使得人们更加坚信他是被保守派暗杀的。
维克多-崔死亡的消息传出后,苏联五个姑娘为他自杀,更多更多的年轻人前来希望能和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小小的利加市立医院淹没在人山人海和玫瑰花海中,因为歌迷极度狂热的举动,葬礼仪式被迫延期举行。
随着维克多-崔的去世,KINO乐队自然解散。因为乐队所有的作词、作曲、编曲和专辑制作都是维克多-崔一个人操办,没有他的KINO根本无法存在下去。
不过他和歌迷约定的新专辑《乔尔尼(Черний)》还是如期面世,乔尔尼在俄语里面是黑色的意思。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销售一空,黑市里的价格就是抬高到了原价的10倍,还是供不应求。包括这张遗作,维克多-崔一共完成了10张专辑和4部电影。
在他死后,彼得堡艺术家们筹款在他的墓地上制作了追悼碑,苏联各地还陆续出现了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的街道。特别是莫斯科的艺术街道老阿尔巴特街2号出现了他的追悼墙(又名痛哭之墙),墙壁上写满了歌迷对他的思念。“维克多!你永远在我们的心脏里。”“维克多!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歌曲或许不能改变世界,但维克多-崔改变了我们。”
每年8月15日,俄罗斯的摇滚乐队会自发的召开维克多-崔纪念演出。1993年,维克多-崔成为莫斯科明星广场殿堂的一员,排在苏联永远的国民歌手布索茨基之后。还被选为对perestroyka(苏联改革)最闪亮的星星,成为改变苏联历史的13名为人中的一员。
不久前莫斯科市议会还批准在莫斯科大学附近建立“伟大的摇滚歌手维克多-崔建筑纪念碑”铜像,铜像的造型决定采用维克多-崔戴着墨镜,光脚骑着亚巴(80年代古老的摩托车)的模样。
“如果所有人都在睡觉,那会有谁去唱歌?”——维克多-崔
by Sabrina Jaszi & Steve Huey
One of Russia's most popular rock bands, Kino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Gorbachev era of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and struck a nerve with many Soviet youths longing for a brighter, freer future. The group's legend was tragically cemented when frontman Victor Tsoi (sometimes Tsoy) was killed in a car crash in 1990, sparking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grief rivaling that of icons like Kurt Cobain or John Lennon. The group remains an object of cultish adulation, manifested in graffiti, memorials, and tributes by lone guitar players in underground walkways throughout the former U.S.S.R.
As a 19-year-old, Tsoi formed the first version of Kino in his hometown of St. Petersburg (then Leningrad) in 1981, along with Alexei Ribin and Oleg Valinsky. In its first incarnation the group was called Garin i Giperboloidy (Garin and the Deathray) but one year later became Kino. The Soviet regime considered rock music a threat to its tenets of collectivism and uniformity, so Kino, like all groups of the time, was forced into the semi-anonymity of underground clubs and gatherings at friends' apartments. These so-called kvartirniks were often referenced by Tsoi in his compositions, as were other details of life under Soviet rule recognizable to listeners.
The chance meeting on a St. Petersburg local train (elektrichka) between Tsoi and Akvarium's Boris Grebenshikov led to the recording of Kino's first album. Grebinshivkov overheard Tsoi playing the song &Vse Moi Druzya Idut Marsham& (All My Friends Go Marching By) en route from one of his concerts and introduced the young musician to Andrei Tropillo, director of Lenningrad's first independent recording studio. Akvarium provided the muscle for Kino's 1982 debut, 45. After its release, the trio moved to Moscow and splintered; Ribin left in 1983, leaving Tsoi to complete their second album, 46.
In 1984, Tsoi formed a new version of Kino with guitarist Yuri Kasparyan, bassist Alexander Titov, and drummer Georgi Guriyanov; they debuted on that year's Nachal'nik Kamchatki (The Master of Kamchatka). A performance at St. Petersburg's second annual rock festival heralded their return, and their next two albums, 1985's Eto Nye Lyubov (This Is Not Love) and 1986's Noch (The Night), saw their reputation steadily growing. Perestroika under way, Gorbachev's new policy of glasnost ended the group's confinement to the underground and spurred them into the realm of national renown. Their sound had matured, branching away from Russian bard music, and more and more resembled American alternative rock, particularly R.E.M. and the icier side of the Cure. In particular, Noch, for which Tsoi engineered a sound emulating Duran Duran, made a great impact on audiences.
Tsoi began to pursue an acting career on the side in 1986, and bassist Igor Tikhoromirov eventually replaced Titov. In 1987 Kino first shared the stage with American Joanna Stingray, who would later marry guitarist Yuri Kasparyan and implement the recognition of Soviet rock in the States by producing the 1989 Red Wave: 4 Underground Bands from the USSR compilation; the album included six songs from Noch. Tsoi's film career was also picking up with the 1987 release of Assa, whose soundtrack included the song &(We're Waiting For) Change&; it would subsequently become a teen anthem and the group's biggest hit.
In 1988, the band released its most polished album, Gruppa Krovi (Blood Type), which even got a favorable write-up in The Village Voice in America. Tsoi pursued his film career, starring in Igla (The Needle), which was the second-highest-grossing film in the U.S.S.R. for the year 1988 and featured songs from Gruppa Krovi and the group's upcoming 1989 release Zvezda Po Imene Solntse (A Star Named the Sun). For the film's premier, Tsoi and Kasparyan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layed their first and only American show.
On June 24, 1990, Kino played its last concert, for a crowd of 62,000. Tsoi died tragically in an auto accident in Riga, Latvia, on August 15, 1990. The band's unfinished album was released afterward as Cherniy Albom (Black Album). After the untimely death of its lead singer, the group gained legendary status. Tsoi lives on as the original catalyst of Russian rock & roll.
在中国,崔健(朝鲜族)被称为中国的摇滚之父。在前苏联,也有一位姓崔,民族也和崔健一样的摇滚之父——叫维克多-崔。6月21日是前苏联最后的英雄维克多-崔的生日,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特撰写此文。
这世界上有一些已经去世了但并没有消失的人,在人类的历史中一同呼吸,时常被记起的那些人,我们称他们为英雄。在已经解体的前苏联,有一个被称为最后的英雄的人。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伟大的思想家或是宗教人,更不是军功卓越的军人,他仅仅只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已。为什么俄罗斯的年轻人把他称之为最后的英雄?为什么在阿尔巴特2号他的追悼壁(又名痛哭之壁)前面至今还在响彻他的歌曲?为什么人们继续在书写怀念他的悼文?为什么他的墓碑前面的鲜花每天都是新鲜的?
维克多-崔1962年6月21日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基乌尔达,父亲是韩裔崔东烈、母亲是乌克兰出生的瓦莲齐娜-巴锡尔耶夫娜。在他5岁时,全家搬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日后在他去世后,从前苏联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就他的国籍问题进行过争论。最后这场争论以国籍为俄罗斯,但标明出生地为哈萨克斯坦终结。不过至今哈萨克斯坦人很骄傲的认为维克多-崔就是哈萨克斯坦人,而且把他列为代表哈萨克斯坦的13名伟人之一。
对画画有着天赋的维克多-崔考上了谢洛夫美术学校。除了画画,他在文学和音乐方面更显示出过人的天赋,15岁就开始自己作词作曲。1974年在学校里和马克西姆·巴徐科夫组织了名叫“第六病室”的摇滚乐队。但摇滚在当时的苏联体制下是被视为反国家歌曲,维克多-崔也因为演奏摇滚乐的理由被学校勒令退学。被美术学校勒令退学后,维克多-崔考上列宁格勒市立第61技术专门学校,学习木刻。在学校里遇到阿列塞-鲁宾、奥列格-巴利斯基等人,1981年组织了名叫 “加林和双曲线”(Гарин и Гиперболоиды)的乐队。在这个时期,遇到初恋情人阿鲁卡基娜,尝到了爱情带来的酸甜苦辣滋味,《8年级女学生》就是为阿鲁卡基娜所作。
在偶然的机会下,维克多-崔遇到俄罗斯当代最出色的摇滚乐队“阿科瓦里姆(Akvarium)”的主唱鲍里斯-格列本许科夫。在鲍里斯的影响下加盟摇滚乐队协会,通过与其他著名摇滚乐队的交流,更加丰富了自己的音乐元素。而对维克多-崔慧眼相识的鲍里斯不惜屈尊出任了维克多-崔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当时因为奥列格-巴利斯基退出,维克多-崔组成了崭新的乐队,即成为旧苏联历史上最伟大摇滚乐队的KINO(意为电影)。在第一张专辑推出一个月之前,维克多-崔开始和马莲娜同居,马莲娜也出任了初期KINO的经纪人。和马莲娜的同居也有很多波折,最大的理由是马莲娜的父母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没有正当收入,又是黑头发黄皮肤的韩裔小伙子。在艰苦的情况下终于完成录音,1982年KINO的第一张专辑《KINO45》出世。后面的45据说是因为演奏时间共45分钟,维克多-崔即兴打上去的。不过第一张专辑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维克多-崔的生活依旧拮据。因为搞摇滚,维克多-崔未能正式毕业第61技术专门学校,以结业的形式走出校门。不过如今市立第61技术专门学校走廊正面,挂着最值得骄傲的毕业生维克多-崔的照片,整个学校里的装饰几乎都是维克多-崔的作品。
1982年,维克多-崔和KINO发表了第二张正式大碟《不著名的歌曲们》,这张专辑中有维克多-崔早期成名曲之一的“最后的英雄”。
1983年KINO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摇滚乐队大奖赛,不过因为主办方不可理解的判分,KINO遭到惨败。因为此事,KINO内部出现分裂,阿列塞-鲁宾退出了乐队。不过他的磨难并没有结束。1984年和马莲娜正式结婚后,维克多-崔肩负一家之主的重担,除了摇滚以外,还得干活养家。千辛万苦之下找到的是坎察特卡锅炉室的火炉工工作,在这里维克多-崔边干活边作歌,完成了第四张专辑《坎察特卡的队长》。在他死后,这个小小的锅炉室成为了象征俄罗斯自由和抵抗的圣地。(注:第三张专辑《KINO46》,其实是第四张专辑的DEMO版本)
1984年维克多-崔和KINO参加第二届摇滚乐队大奖赛,一举获得大奖,1985年再次蝉联这个荣誉。1985年还发生了维克多-崔认为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儿子阿列山德罗-崔来到这个世界上。
虽然已经推出了四张专辑,不过维克多-崔依旧还是没有被大众认可的地下音乐人。遭受着贫穷的折磨,1985年KINO倾尽浑身之力完成了专辑《Noch》,但因为和录音师的摩擦未能在当年出版,转而推出了第五张专辑《这不是爱情》。市场对这张专辑的反应,和前几张一样,还是冷冷淡淡。
1986年,本该作为第五张专辑的《Noch》终于出版。因为连连遭遇失败,谁都没有对这张专辑抱以希望。不过这张专辑出人意料的成为市场的新宠,推出两个月售出50万张,再过几个月销量达到了惊人的200万张。
维克多-崔的歌曲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除了简明有力的曲风以外,反映了当时年轻人心声的歌词更是主要原因,这一点上维克多-崔和崔健有极为相似的地方。“血液型”是维克多-崔最经典的代表曲,看一看歌词:“温柔的安乐窝,不过街道在等待我们的脚步 / 军靴上面如星光的尘埃…… / 舒适的沙发、格子纹络的沙发套、没有按时扣动的扳机 / 阳光照耀的日子只是在灿烂的睡梦中 / 虽然有付出代价的手段,但我不希望廉价的胜利 / 谁的胸膛我也不想践踏 / 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我只是希望和你留在一起 / 不过天上高高的星星召唤我上路 / 我的袖口上记着血液型 / 我的袖口上有我的军号 / 为冲向战场的我祈祷吧,为我祈祷吧 / 不要让我留在原野上 / 不要让我躺在原野上 / 祈祷我的胜利,为我的胜利祈祷吧”
年轻人马上能读解了这个歌词中隐藏的意义,即“这个世界就是你们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得由你们自己来改变。战斗吧!不要躺在荒凉的原野上,尽情战斗吧!我会和你在一起,祈祷着战斗的胜利和幸运……”家家传出了这首歌,年轻人们在大街上高声唱起了这首歌,KINO热潮如旋风般瞬间占领了苏联全国。
有一个插曲能反应他们当时的人气。KINO受邀去切利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进行演出,坐了长长的时间到达切利亚宾斯克的KINO一行,被对他们持有反感的车站工作人员带到警察局。警察局命令他们马上回到列宁格勒,并软禁了他们。无可奈何的KINO一行却从窗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情景,手持蜡烛的年轻人们正包围着警察局。这些年轻人是邀请KINO的大学生,听到KINO被软禁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进行蜡烛示威。“把KINO还给我们!”“我们要维克多-崔!”警察局长面对这样声势浩大的示威,担心会演变成暴动,只好允许KINO的公演。在蜡烛示威队的护送下,KINO来到大学,过不多久操场上想起了维克多-崔和学生们齐声喊唱的“血液型”歌声。为了维克多-崔,苏联年轻人们勇敢的挑战警察局这个国家权力机构,并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变化就这样在开始。
1989年推出的第八张专辑《最后的英雄》中,收录着维克多-崔两大代表曲之一的“变化”(另一曲为“血液型”)。这首歌的歌词十分简明的反应了当时苏联年轻人对自由的意志:代替热气的绿色的玻璃 / 待其火焰的袅袅烟火 / 月历中的一天就这样消亡 / 红色的太阳燃尽 / 一天也随着燃尽 / 燃烧的都市里落下夜色 / 变化!我们的心脏在要求 / 变化!我们的眼睛在要求 / 在我们的笑容和我们的眼泪中 / 还有我们静脉的脉搏里 / 变化!我们等待变化
同一年维克多-崔拿出了第九张专辑《名叫太阳的星星》,这张专辑在俄罗斯卖出500万张,不过考虑到当时盗版猖獗的情况,可以说最少卖出了2000万张。1990年6月24日,旧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在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发生,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为了KINO乐队的公演燃起。在和创下纪录的10多万观众一起,维克多-崔唱起了“血液型”,尤其是唱最后一曲“变化”的时候,整个体育场因为歌声在颤动。结束最后一曲后,维克多-崔想歌迷摇手致意,说了最后一句话。“过不多久的夏天,新专辑就出来了,到时候再见。”
不过,维克多-崔未能遵守这个诺言。因为一个月后,维克多-崔因为交通事故,离开了人世。
“我们是率先成熟的果子,死神会率先扑向我们。”——维克多-崔
1990年8月,维克多-崔接到了让他兴奋异常的消息,爷爷的国家韩国向他发出了演出邀请。“就是推掉其它演出,韩国我一定要去”,接到邀请后的维克多-崔兴奋的向周围人说。因为韩国是维克多-崔一直向往的地方,那里有着他的根。
1990年8月,维克多-崔到拉脱维亚首都利加拍摄MTV并抽空度假。8月15日,钓完鱼开着车回到宾馆的路上,对面开来的大巴从正面全力冲向他的小轿车,把他的轿车往后撞退了10多米,28岁的天才当场死亡。
维克多-崔的死亡充满着重重迷雾,因为当局对事故的调查极为匆匆,肇事司机没几天就被释放,然后失去行踪,以至人们猜测这是KGB的所为。其实维克多-崔早已是当时苏联政府的眼中钉,他的歌曲尤为注重歌词。其尖锐的歌词破坏力极强,有些人甚至拿他的歌词和俄罗斯夭折天才诗人叶赛宁的诗相提并论。他的歌词,不,应该说是他的诗,具备了极强的感染力。他的以这个力量为基础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苏联年轻人心灵深处,使他成为了自由和抵抗的化身。他对年轻人的巨大影响,是保守派极度不愿看到的。
维克多-崔还被认为是影响戈尔巴乔夫的5人之一,戈尔巴乔夫曾约见维克多-崔,握着手说:“同志,为了perestroyka(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一起努力吧。”因为他的歌曲是perestroyka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是作为强硬保守派的KGB暗杀他的充分理由。
维克多-崔去世后的第二天,苏联所有激进派报纸都大大报道了他的死亡,但保守派的报纸则只字不提。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如此鲜明,使得人们更加坚信他是被保守派暗杀的。
维克多-崔死亡的消息传出后,苏联五个姑娘为他自杀,更多更多的年轻人前来希望能和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小小的利加市立医院淹没在人山人海和玫瑰花海中,因为歌迷极度狂热的举动,葬礼仪式被迫延期举行。
随着维克多-崔的去世,KINO乐队自然解散。因为乐队所有的作词、作曲、编曲和专辑制作都是维克多-崔一个人操办,没有他的KINO根本无法存在下去。
不过他和歌迷约定的新专辑《乔尔尼(Черний)》还是如期面世,乔尔尼在俄语里面是黑色的意思。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销售一空,黑市里的价格就是抬高到了原价的10倍,还是供不应求。包括这张遗作,维克多-崔一共完成了10张专辑和4部电影。
在他死后,彼得堡艺术家们筹款在他的墓地上制作了追悼碑,苏联各地还陆续出现了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的街道。特别是莫斯科的艺术街道老阿尔巴特街2号出现了他的追悼墙(又名痛哭之墙),墙壁上写满了歌迷对他的思念。“维克多!你永远在我们的心脏里。”“维克多!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歌曲或许不能改变世界,但维克多-崔改变了我们。”
每年8月15日,俄罗斯的摇滚乐队会自发的召开维克多-崔纪念演出。1993年,维克多-崔成为莫斯科明星广场殿堂的一员,排在苏联永远的国民歌手布索茨基之后。还被选为对perestroyka(苏联改革)最闪亮的星星,成为改变苏联历史的13名为人中的一员。
不久前莫斯科市议会还批准在莫斯科大学附近建立“伟大的摇滚歌手维克多-崔建筑纪念碑”铜像,铜像的造型决定采用维克多-崔戴着墨镜,光脚骑着亚巴(80年代古老的摩托车)的模样。
“如果所有人都在睡觉,那会有谁去唱歌?”——维克多-崔
by Sabrina Jaszi & Steve Huey
One of Russia's most popular rock bands, Kino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Gorbachev era of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and struck a nerve with many Soviet youths longing for a brighter, freer future. The group's legend was tragically cemented when frontman Victor Tsoi (sometimes Tsoy) was killed in a car crash in 1990, sparking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grief rivaling that of icons like Kurt Cobain or John Lennon. The group remains an object of cultish adulation, manifested in graffiti, memorials, and tributes by lone guitar players in underground walkways throughout the former U.S.S.R.
As a 19-year-old, Tsoi formed the first version of Kino in his hometown of St. Petersburg (then Leningrad) in 1981, along with Alexei Ribin and Oleg Valinsky. In its first incarnation the group was called Garin i Giperboloidy (Garin and the Deathray) but one year later became Kino. The Soviet regime considered rock music a threat to its tenets of collectivism and uniformity, so Kino, like all groups of the time, was forced into the semi-anonymity of underground clubs and gatherings at friends' apartments. These so-called kvartirniks were often referenced by Tsoi in his compositions, as were other details of life under Soviet rule recognizable to listeners.
The chance meeting on a St. Petersburg local train (elektrichka) between Tsoi and Akvarium's Boris Grebenshikov led to the recording of Kino's first album. Grebinshivkov overheard Tsoi playing the song &Vse Moi Druzya Idut Marsham& (All My Friends Go Marching By) en route from one of his concerts and introduced the young musician to Andrei Tropillo, director of Lenningrad's first independent recording studio. Akvarium provided the muscle for Kino's 1982 debut, 45. After its release, the trio moved to Moscow and splintered; Ribin left in 1983, leaving Tsoi to complete their second album, 46.
In 1984, Tsoi formed a new version of Kino with guitarist Yuri Kasparyan, bassist Alexander Titov, and drummer Georgi Guriyanov; they debuted on that year's Nachal'nik Kamchatki (The Master of Kamchatka). A performance at St. Petersburg's second annual rock festival heralded their return, and their next two albums, 1985's Eto Nye Lyubov (This Is Not Love) and 1986's Noch (The Night), saw their reputation steadily growing. Perestroika under way, Gorbachev's new policy of glasnost ended the group's confinement to the underground and spurred them into the realm of national renown. Their sound had matured, branching away from Russian bard music, and more and more resembled American alternative rock, particularly R.E.M. and the icier side of the Cure. In particular, Noch, for which Tsoi engineered a sound emulating Duran Duran, made a great impact on audiences.
Tsoi began to pursue an acting career on the side in 1986, and bassist Igor Tikhoromirov eventually replaced Titov. In 1987 Kino first shared the stage with American Joanna Stingray, who would later marry guitarist Yuri Kasparyan and implement the recognition of Soviet rock in the States by producing the 1989 Red Wave: 4 Underground Bands from the USSR compilation; the album included six songs from Noch. Tsoi's film career was also picking up with the 1987 release of Assa, whose soundtrack included the song &(We're Waiting For) Change&; it would subsequently become a teen anthem and the group's biggest hit.
In 1988, the band released its most polished album, Gruppa Krovi (Blood Type), which even got a favorable write-up in The Village Voice in America. Tsoi pursued his film career, starring in Igla (The Needle), which was the second-highest-grossing film in the U.S.S.R. for the year 1988 and featured songs from Gruppa Krovi and the group's upcoming 1989 release Zvezda Po Imene Solntse (A Star Named the Sun). For the film's premier, Tsoi and Kasparyan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layed their first and only American show.
On June 24, 1990, Kino played its last concert, for a crowd of 62,000. Tsoi died tragically in an auto accident in Riga, Latvia, on August 15, 1990. The band's unfinished album was released afterward as Cherniy Albom (Black Album). After the untimely death of its lead singer, the group gained legendary status. Tsoi lives on as the original catalyst of Russian rock & roll.
si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