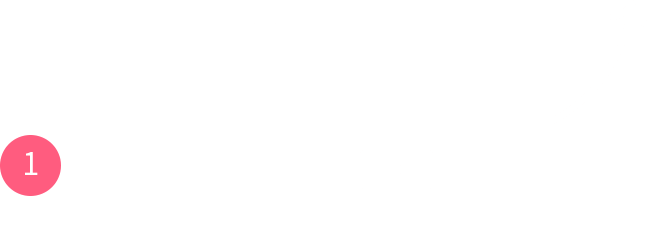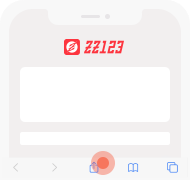甲: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作的。
乙:是啊!
甲:能写。
乙:哦。
甲:过去呀,艺人哪,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乙:可不是嘛。
甲:撂土地。
乙:哎,没有上舞台的。
甲:没有多大学问。
乙:是吗?
甲:不会写字儿。解放以后,学文化、学政治。
乙:哎。
甲: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啦!
乙:是嘛。
甲: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作家。
乙:作家?
甲:不简单哪。
乙: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甲:有!
乙:谁呀?
甲:我。
乙:你?
甲:啊。
乙: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甲: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乙:这我倒没注意。
甲:没注意?
乙:啊!
甲:我净在家里坐着。
乙:噢,家里坐着呀!你就这么个“坐家”呀?
甲:正在家里作着呢。
乙:您得说呀,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甲:哎,写着呢,写作嘛。
乙:哎,写作。
甲: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乙:是嘛。
甲:你要过去哪行?过去艺人,天桥撂土地。
乙:可不是嘛。
甲:累一天,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棵白菜的。
乙:收入啊,就那么少。
甲:就是啊,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乙: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
甲: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乙: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甲:收入不多呀!
乙:怎么呢!
甲:买票的主儿少。
乙:买票的主儿少?
甲: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竟是摇头票。
乙:什么叫“摇头票”?
甲:那会儿剧场里不查票吗?
乙:是啊。
甲:到时候下去查票去,“先生,您这儿有票吗?”你看他这劲儿,翻眼、一摇头。完啦!
乙:这个是怎么意思呢?
甲:这个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乙: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甲:他不说还好啊,他一说你更倒霉啦!
乙:怎么?
甲:他说话?“先生,您这是?有票吗?”“哼!全是我带来的!”
乙:全是他带来的。
甲: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啦!
乙:那就全白听啦?
甲:那年头就这样。
乙:嘿,您说那个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甲: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啦!
乙:怎么?
甲:你像刘宝全、白云鹏啊,金万昌啊,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乙:帝制时代是有皇上时候。
甲:那年头儿,名演员进宫当皇差。
乙:对呀。
甲:给皇上家唱去。
乙:是啊。
甲:特别是那个西太后,给她唱去。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乙:发啦?
甲:发啦!
乙:那么演员犯什么罪啦?
甲:什么叫犯什么罪呀?瞧你长得别扭。
乙:噢,这就给发啦!
甲:哎,什么样儿啊?黑了咕叽的,发啦!
乙:这玩艺儿,发啦!
甲:你还甭说皇上家,你就说做大官儿的家里头,他家有喜寿事叫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有不许说的,可别说。
乙:这叫忌字儿。
甲:哎,忌讳。哎,老爷的名字叫官讳。
乙:那能说吗?
甲:不能说。忌讳嘛。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剐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乙:噢,这也不能说。
甲:哎!
乙:你瞧,说相声的就难啦!
甲:难啦,说相声拿谁逗哏呢?拿自己开玩笑吧!
乙:也就那样啦!
甲:“这回咱们俩说段相声,说不好啊,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乙:对。
甲:“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啊。”
乙:这话没错啦!
甲:老爷生气啦!
乙:这他生什么气呀?
甲:老爷小名儿叫“狗子”。
乙:这谁能知道啊?
甲:就说是啊。在那年头做艺更难啦!
乙:是吗?
甲: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儿,这就说起来。
乙:噢,道边儿上。
甲: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儿官来了。看街的一喊:“闲人散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呼噜”——全跑啦!
乙:噢,这人都散啦!
甲:官来了,谁不怕?
乙:那么,没有给钱的啦?
甲: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呀?
乙:这话对呀。
甲:就是这样的生活,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乙:怎么?
甲:皇上家有祭日。斋祭辰,禁止娱乐。
乙:禁止娱乐,怎么样?
甲:歇工。
乙:他有他的祭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吗?
甲: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乙:就得歇工。
甲:哎,皇上要死啦,你就更倒霉啦!皇上死啦,有国服啊。
乙:就是皇上死啦。死啦倒好啦!
甲:啊?
乙:死了就死了吧?
甲:啊,你倒蛮大方。“死了就死了吧!”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啦!杀头!
乙:这怎么有罪啦?
甲:轻君之罪。
乙:怎么啦?
甲:皇上死啦,不能说死。
乙:说什么?
甲:专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乙:那“死”说什么?
甲:死了叫“驾崩”。
乙:驾崩?
甲:哎!
乙:这俩字怎么讲啊?
甲:“驾崩”啊?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啦!”
乙:“架出去崩啦?”
甲:反正是好字眼儿吧!
乙:哎,是好字眼儿。
甲: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上死了,一百天国服。
乙:噢,就禁止娱乐。
甲:人人都得穿孝。
乙:那是啊。
甲:男人不准剃头,妇女不准搽红粉。
乙:挂孝吗!
甲:不能穿红衣服。
乙:那是啊!
甲: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乙:干什么?
甲:穿孝嘛。
乙:挂孝。
甲:家里房子那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乙: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甲:那年头就那么专制。
乙:太厉害啦!
甲:卖菜都限制嘛。
乙:卖菜受什么限制啊?
甲: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卖胡萝卜不行。
乙:胡萝卜怎么不行呢?
甲:红东西不准见。
乙:那它就那么长来的。
甲:你要卖也行啊,得做蓝套儿把它套起来。
乙:套上?我还没见过套上卖的呢?
甲:那年头儿吃辣椒都是青的。
乙:没有红的?
甲:谁家种了辣椒一看是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了。
乙:别埋呀,卖去呀!
甲:不够套儿钱!
乙: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甲:商店挂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红的,换蓝的。
乙:也得换蓝的?
甲: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赤红脸儿都不许出门儿。
乙:那可没办法!这是皮肤的颜色!
甲:出门不行。我听我大爷说过,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乙:鼻子是红的?
甲:出去买东西去啦。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儿?”
乙: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儿?
甲:“没事呀,我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知道!您看,没剃头哇。”“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儿?”“鼻子是红了点儿,天生长的,不是现弄的。”“不让出门儿。”“不让出门儿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要出门来也行啊,把鼻子染蓝了!”
乙:染了?
甲:那怎么染哪?
乙:那没法染。
甲:就是啊,弄蓝颜色把脸涂上,更不敢出去啦!
乙:怎么?
甲:成窦尔墩啦!
乙:好嘛!
甲: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乙:全歇了?
甲: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啦!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乙:改行啦?那么您说说都什么人改行啦?
甲: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乙:好啊。
甲:那年头,不让唱啦!
乙:改行啦?
甲:改行啦。
乙:干吗去啦?
甲:卖粥。
乙:卖粥?
甲:北京的早点啊,粳米粥,沙锅熬的粳米粥。烧饼、麻花、煎饼馃子。
乙:下街卖粥。
甲:哎,就在口上摆摊儿。
乙:瞧瞧,那玩艺儿得会吆喝。
甲:就是啊!
乙:还得……填难。
甲: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艺术家他哪会吆喝呀?
乙:不会呀?
甲: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嗓子都不敢遛,借这机会遛遛嗓子。
乙:唱什么呀?
甲:自己会编词儿,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乙:是啊,唱大鼓得有鼓啊。
甲:他不有那沙锅嘛。
乙:噢,沙锅就当鼓。
甲:哎。
乙:打鼓这个鼓楗子呢?
甲:没有啊,有勺。
乙:那么这个鼓板哪?
甲:没板,拿套烧饼馃子。
乙:嘿,他倒会对付。
甲:一和弄这粥。(学过门儿,唱)“吊炉烧饼扁又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粳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老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把钱赚,所为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
乙:怎么啦?
甲:沙锅碎啦。
乙:沙锅碎啦!
甲: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都不行。
乙:他被生活挤兑的嘛。
甲: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乙:哪位呀?
甲:唱老旦的龚云甫。
乙:哦,龚云甫。
甲:老旦唱的最好。拿手戏呀,是《遇后》、《龙袍》。
乙:不错呀!
甲:后台一叫板——“苦啊!”
乙:就这句。
甲:是可堂的彩声。
乙:真好听啊。
甲:那年头不让唱啦!
乙:也改行啦?
甲:卖菜去啦。
乙:卖青菜去啦?哎哟!那可不容易。
甲:是吗?
乙:头一样说,你得有那么大力气。
甲: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担挑。担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走起来这人得精神,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乙:菜怎么还精神呢?
甲:内行卖菜嘛,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泥土冲下去。上足了水,你看那菜看着就精神。那韭菜多细呀,一捆儿,啪!往那一戳,你看韭菜那样。
乙:倍儿挺!
甲:你不信晒它俩钟头,全趴下啦。
乙: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甲: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乙:那是啊。
甲:北京的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的一样。嘿,那个好听。
乙:是啊。
甲: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儿吆喝出来。
乙:您学一学怎么吆喝。
甲:吆喝出来这味儿,(学叫卖声)“香菜辣蓁椒哇,沟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红萝卜、卞萝卜、嫩芽的香椿啊、蒜来好韭菜呀。”
乙:吆喝的好听。
甲:这外行哪干得了啊?
乙:是啊。
甲: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乙:对呀,
甲:老旦唱的好,干这不行。
乙:外行。
甲:没办法。弄份挑子,买了几样菜,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乙: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甲:习惯啦!遛了半天没开张。
乙:怎么会没人买呢?
甲: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乙:原因是什么呢?
甲:他不吆喝。
乙:那哪开得了张啊。
甲: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乙:那是啊!
甲:自己也会编词儿,一看所卖的菜,编了几句,吆唱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乙:您学一学。
甲:(学)“唉!台台台令台今台……”(小锣凤点头)
乙:还带着家伙呢!
甲:走道儿的都奇怪啦!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呢!
乙:是吗?
甲:吆喝出来好听!
乙:怎么吆喝的?
甲:(唱二簧散板)“香菜、芹菜辣蓁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
乙: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甲:真出来一个买主。
乙:哦,开张啦。
甲:出来一个老太太买黄瓜,“卖黄瓜的过来,买两条。”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乙:那也得卖给人家呀!
甲:总算开了张吧!
乙:对呀!
甲:北京的老太太买黄瓜麻烦,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她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乙:她干吗尝尝啊?
甲:不甜她不要,“过来买两条啊!”把挑儿挑过来,往这儿一放,他一扶肩膀这个疼啊。
乙:压的嘛。
甲:他想起那叫板来啦,
乙:哪句呀?
甲:“唉!苦啊!”老太太误会啦!
乙:怎么?
甲:黄瓜苦的?不要啦!
乙:嗨!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啦!
甲: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啦。
乙:哪位呀?
甲:金少山。
乙:嗬,那花脸可好!
甲:唱的好!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乙:是啊。
甲:那年头儿,不让唱,改行啦!
乙:他干什么去啦?
甲:卖西瓜。
乙:卖整个的?
甲:门口摆摊儿。
乙:摆摊儿是卖零块儿。
甲:哎。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手推车往这儿一顶,上面搭好板子,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潲湿了。
乙:瞅着那么干净。
甲:用草圈把西瓜码起来,你看着就凉快。切西瓜刀,一尺多长、二寸多宽,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先卖半个,上面搁半个做广告。让你走这儿一瞧:嗬,西瓜好啊!吃两
块。切开这西瓜一瞧:生的?塞了边儿。
乙:那就不要啦?
甲: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乙:噢,蒙人呢?
甲: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学叫卖声)“吃来呗闹块咧,哎杀着你的口儿甜咧,两个大子儿咧,吃来呗闹块尝啊。”
乙:哎,就这么吆喝。
甲:这是内行。这位唱花脸的,外行啊。
乙: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甲:做小买卖不行啊,门口买八个西瓜,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乙:刀哪?
甲: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乙:切菜刀切西瓜?
甲:切出来有块儿大、有块儿小。
乙:他不会切呀。
甲: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乙:是啊。
甲:他一块儿八个全宰啦!
乙:他倒急性子。
甲:唱花脸的架子,攥着切菜刀,往那儿一站,看着西瓜,这样!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啦!
乙:是瘆人。
甲:走他跟前儿吓一跳。
乙:这位愣住啦!
甲:怎么回事?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儿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儿走吧!
乙:怎么绕着走啦?
甲: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这怎么回事?他跟谁呀?
乙:不知道。
甲:他跟前儿没人。
乙:是啊。
甲:大概是对门儿的。
乙:这位还胡琢磨。
甲:他站这儿这么一看:老远好几十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乙:过来吃?
甲:你那样,谁敢过去呀?
乙:说的是呢。
甲: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啦!
乙:唱?
甲:可是卖西瓜的词儿,一叫板就这样。“哼……!”
乙:叫板呢。
甲:往后点儿吧!
乙:躲开吧。
甲:(学京剧摇板)“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旱秧脆沙瓤。一子儿一块不要谎,你们要不信请尝尝!(白)你们吃啊!”
乙:吃!
甲:全给吓跑啦!
乙:那还不跑!
甲: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作的。
乙:是啊!
甲:能写。
乙:哦。
甲:过去呀,艺人哪,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乙:可不是嘛。
甲:撂土地。
乙:哎,没有上舞台的。
甲:没有多大学问。
乙:是吗?
甲:不会写字儿。解放以后,学文化、学政治。
乙:哎。
甲: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啦!
乙:是嘛。
甲: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作家。
乙:作家?
甲:不简单哪。
乙: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甲:有!
乙:谁呀?
甲:我。
乙:你?
甲:啊。
乙: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甲: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乙:这我倒没注意。
甲:没注意?
乙:啊!
甲:我净在家里坐着。
乙:噢,家里坐着呀!你就这么个“坐家”呀?
甲:正在家里作着呢。
乙:您得说呀,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甲:哎,写着呢,写作嘛。
乙:哎,写作。
甲: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乙:是嘛。
甲:你要过去哪行?过去艺人,天桥撂土地。
乙:可不是嘛。
甲:累一天,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棵白菜的。
乙:收入啊,就那么少。
甲:就是啊,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乙: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
甲: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乙: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甲:收入不多呀!
乙:怎么呢!
甲:买票的主儿少。
乙:买票的主儿少?
甲: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竟是摇头票。
乙:什么叫“摇头票”?
甲:那会儿剧场里不查票吗?
乙:是啊。
甲:到时候下去查票去,“先生,您这儿有票吗?”你看他这劲儿,翻眼、一摇头。完啦!
乙:这个是怎么意思呢?
甲:这个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乙: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甲:他不说还好啊,他一说你更倒霉啦!
乙:怎么?
甲:他说话?“先生,您这是?有票吗?”“哼!全是我带来的!”
乙:全是他带来的。
甲: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啦!
乙:那就全白听啦?
甲:那年头就这样。
乙:嘿,您说那个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甲: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啦!
乙:怎么?
甲:你像刘宝全、白云鹏啊,金万昌啊,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乙:帝制时代是有皇上时候。
甲:那年头儿,名演员进宫当皇差。
乙:对呀。
甲:给皇上家唱去。
乙:是啊。
甲:特别是那个西太后,给她唱去。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乙:发啦?
甲:发啦!
乙:那么演员犯什么罪啦?
甲:什么叫犯什么罪呀?瞧你长得别扭。
乙:噢,这就给发啦!
甲:哎,什么样儿啊?黑了咕叽的,发啦!
乙:这玩艺儿,发啦!
甲:你还甭说皇上家,你就说做大官儿的家里头,他家有喜寿事叫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有不许说的,可别说。
乙:这叫忌字儿。
甲:哎,忌讳。哎,老爷的名字叫官讳。
乙:那能说吗?
甲:不能说。忌讳嘛。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剐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乙:噢,这也不能说。
甲:哎!
乙:你瞧,说相声的就难啦!
甲:难啦,说相声拿谁逗哏呢?拿自己开玩笑吧!
乙:也就那样啦!
甲:“这回咱们俩说段相声,说不好啊,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乙:对。
甲:“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啊。”
乙:这话没错啦!
甲:老爷生气啦!
乙:这他生什么气呀?
甲:老爷小名儿叫“狗子”。
乙:这谁能知道啊?
甲:就说是啊。在那年头做艺更难啦!
乙:是吗?
甲: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儿,这就说起来。
乙:噢,道边儿上。
甲: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儿官来了。看街的一喊:“闲人散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呼噜”——全跑啦!
乙:噢,这人都散啦!
甲:官来了,谁不怕?
乙:那么,没有给钱的啦?
甲: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呀?
乙:这话对呀。
甲:就是这样的生活,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乙:怎么?
甲:皇上家有祭日。斋祭辰,禁止娱乐。
乙:禁止娱乐,怎么样?
甲:歇工。
乙:他有他的祭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吗?
甲: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乙:就得歇工。
甲:哎,皇上要死啦,你就更倒霉啦!皇上死啦,有国服啊。
乙:就是皇上死啦。死啦倒好啦!
甲:啊?
乙:死了就死了吧?
甲:啊,你倒蛮大方。“死了就死了吧!”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啦!杀头!
乙:这怎么有罪啦?
甲:轻君之罪。
乙:怎么啦?
甲:皇上死啦,不能说死。
乙:说什么?
甲:专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乙:那“死”说什么?
甲:死了叫“驾崩”。
乙:驾崩?
甲:哎!
乙:这俩字怎么讲啊?
甲:“驾崩”啊?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啦!”
乙:“架出去崩啦?”
甲:反正是好字眼儿吧!
乙:哎,是好字眼儿。
甲: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上死了,一百天国服。
乙:噢,就禁止娱乐。
甲:人人都得穿孝。
乙:那是啊。
甲:男人不准剃头,妇女不准搽红粉。
乙:挂孝吗!
甲:不能穿红衣服。
乙:那是啊!
甲: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乙:干什么?
甲:穿孝嘛。
乙:挂孝。
甲:家里房子那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乙: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甲:那年头就那么专制。
乙:太厉害啦!
甲:卖菜都限制嘛。
乙:卖菜受什么限制啊?
甲: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卖胡萝卜不行。
乙:胡萝卜怎么不行呢?
甲:红东西不准见。
乙:那它就那么长来的。
甲:你要卖也行啊,得做蓝套儿把它套起来。
乙:套上?我还没见过套上卖的呢?
甲:那年头儿吃辣椒都是青的。
乙:没有红的?
甲:谁家种了辣椒一看是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了。
乙:别埋呀,卖去呀!
甲:不够套儿钱!
乙: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甲:商店挂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红的,换蓝的。
乙:也得换蓝的?
甲: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赤红脸儿都不许出门儿。
乙:那可没办法!这是皮肤的颜色!
甲:出门不行。我听我大爷说过,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乙:鼻子是红的?
甲:出去买东西去啦。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儿?”
乙: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儿?
甲:“没事呀,我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知道!您看,没剃头哇。”“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儿?”“鼻子是红了点儿,天生长的,不是现弄的。”“不让出门儿。”“不让出门儿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要出门来也行啊,把鼻子染蓝了!”
乙:染了?
甲:那怎么染哪?
乙:那没法染。
甲:就是啊,弄蓝颜色把脸涂上,更不敢出去啦!
乙:怎么?
甲:成窦尔墩啦!
乙:好嘛!
甲: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乙:全歇了?
甲: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啦!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乙:改行啦?那么您说说都什么人改行啦?
甲: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乙:好啊。
甲:那年头,不让唱啦!
乙:改行啦?
甲:改行啦。
乙:干吗去啦?
甲:卖粥。
乙:卖粥?
甲:北京的早点啊,粳米粥,沙锅熬的粳米粥。烧饼、麻花、煎饼馃子。
乙:下街卖粥。
甲:哎,就在口上摆摊儿。
乙:瞧瞧,那玩艺儿得会吆喝。
甲:就是啊!
乙:还得……填难。
甲: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艺术家他哪会吆喝呀?
乙:不会呀?
甲: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嗓子都不敢遛,借这机会遛遛嗓子。
乙:唱什么呀?
甲:自己会编词儿,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乙:是啊,唱大鼓得有鼓啊。
甲:他不有那沙锅嘛。
乙:噢,沙锅就当鼓。
甲:哎。
乙:打鼓这个鼓楗子呢?
甲:没有啊,有勺。
乙:那么这个鼓板哪?
甲:没板,拿套烧饼馃子。
乙:嘿,他倒会对付。
甲:一和弄这粥。(学过门儿,唱)“吊炉烧饼扁又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粳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老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把钱赚,所为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
乙:怎么啦?
甲:沙锅碎啦。
乙:沙锅碎啦!
甲: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都不行。
乙:他被生活挤兑的嘛。
甲: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乙:哪位呀?
甲:唱老旦的龚云甫。
乙:哦,龚云甫。
甲:老旦唱的最好。拿手戏呀,是《遇后》、《龙袍》。
乙:不错呀!
甲:后台一叫板——“苦啊!”
乙:就这句。
甲:是可堂的彩声。
乙:真好听啊。
甲:那年头不让唱啦!
乙:也改行啦?
甲:卖菜去啦。
乙:卖青菜去啦?哎哟!那可不容易。
甲:是吗?
乙:头一样说,你得有那么大力气。
甲: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担挑。担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走起来这人得精神,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乙:菜怎么还精神呢?
甲:内行卖菜嘛,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泥土冲下去。上足了水,你看那菜看着就精神。那韭菜多细呀,一捆儿,啪!往那一戳,你看韭菜那样。
乙:倍儿挺!
甲:你不信晒它俩钟头,全趴下啦。
乙: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甲: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乙:那是啊。
甲:北京的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的一样。嘿,那个好听。
乙:是啊。
甲: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儿吆喝出来。
乙:您学一学怎么吆喝。
甲:吆喝出来这味儿,(学叫卖声)“香菜辣蓁椒哇,沟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红萝卜、卞萝卜、嫩芽的香椿啊、蒜来好韭菜呀。”
乙:吆喝的好听。
甲:这外行哪干得了啊?
乙:是啊。
甲: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乙:对呀,
甲:老旦唱的好,干这不行。
乙:外行。
甲:没办法。弄份挑子,买了几样菜,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乙: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甲:习惯啦!遛了半天没开张。
乙:怎么会没人买呢?
甲: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乙:原因是什么呢?
甲:他不吆喝。
乙:那哪开得了张啊。
甲: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乙:那是啊!
甲:自己也会编词儿,一看所卖的菜,编了几句,吆唱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乙:您学一学。
甲:(学)“唉!台台台令台今台……”(小锣凤点头)
乙:还带着家伙呢!
甲:走道儿的都奇怪啦!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呢!
乙:是吗?
甲:吆喝出来好听!
乙:怎么吆喝的?
甲:(唱二簧散板)“香菜、芹菜辣蓁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
乙: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甲:真出来一个买主。
乙:哦,开张啦。
甲:出来一个老太太买黄瓜,“卖黄瓜的过来,买两条。”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乙:那也得卖给人家呀!
甲:总算开了张吧!
乙:对呀!
甲:北京的老太太买黄瓜麻烦,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她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乙:她干吗尝尝啊?
甲:不甜她不要,“过来买两条啊!”把挑儿挑过来,往这儿一放,他一扶肩膀这个疼啊。
乙:压的嘛。
甲:他想起那叫板来啦,
乙:哪句呀?
甲:“唉!苦啊!”老太太误会啦!
乙:怎么?
甲:黄瓜苦的?不要啦!
乙:嗨!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啦!
甲: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啦。
乙:哪位呀?
甲:金少山。
乙:嗬,那花脸可好!
甲:唱的好!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乙:是啊。
甲:那年头儿,不让唱,改行啦!
乙:他干什么去啦?
甲:卖西瓜。
乙:卖整个的?
甲:门口摆摊儿。
乙:摆摊儿是卖零块儿。
甲:哎。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手推车往这儿一顶,上面搭好板子,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潲湿了。
乙:瞅着那么干净。
甲:用草圈把西瓜码起来,你看着就凉快。切西瓜刀,一尺多长、二寸多宽,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先卖半个,上面搁半个做广告。让你走这儿一瞧:嗬,西瓜好啊!吃两
块。切开这西瓜一瞧:生的?塞了边儿。
乙:那就不要啦?
甲: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乙:噢,蒙人呢?
甲: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学叫卖声)“吃来呗闹块咧,哎杀着你的口儿甜咧,两个大子儿咧,吃来呗闹块尝啊。”
乙:哎,就这么吆喝。
甲:这是内行。这位唱花脸的,外行啊。
乙: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甲:做小买卖不行啊,门口买八个西瓜,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乙:刀哪?
甲: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乙:切菜刀切西瓜?
甲:切出来有块儿大、有块儿小。
乙:他不会切呀。
甲: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乙:是啊。
甲:他一块儿八个全宰啦!
乙:他倒急性子。
甲:唱花脸的架子,攥着切菜刀,往那儿一站,看着西瓜,这样!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啦!
乙:是瘆人。
甲:走他跟前儿吓一跳。
乙:这位愣住啦!
甲:怎么回事?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儿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儿走吧!
乙:怎么绕着走啦?
甲: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这怎么回事?他跟谁呀?
乙:不知道。
甲:他跟前儿没人。
乙:是啊。
甲:大概是对门儿的。
乙:这位还胡琢磨。
甲:他站这儿这么一看:老远好几十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乙:过来吃?
甲:你那样,谁敢过去呀?
乙:说的是呢。
甲: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啦!
乙:唱?
甲:可是卖西瓜的词儿,一叫板就这样。“哼……!”
乙:叫板呢。
甲:往后点儿吧!
乙:躲开吧。
甲:(学京剧摇板)“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旱秧脆沙瓤。一子儿一块不要谎,你们要不信请尝尝!(白)你们吃啊!”
乙:吃!
甲:全给吓跑啦!
乙:那还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