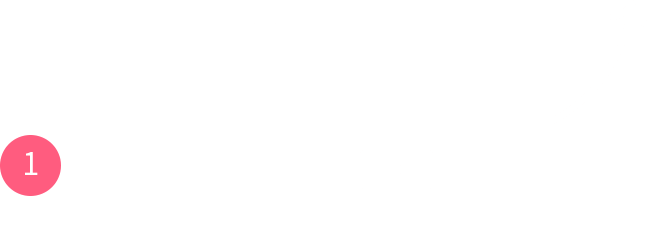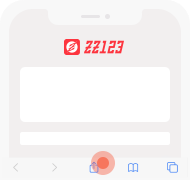posted on:2013 years
play:0 times
duration:07:01
text
lrc text
第六章 小猪和胡椒 她站在小房跟前看了一两分钟,想着下一步该干什么。突然间,一个穿着制服的仆人(她认为仆人是由于穿着仆人的制服,如果只看他的脸,会把他看成一条鱼的)从树林跑来,用脚使劲儿地踢着门。另一个穿着制服,长着圆脸庞和像青蛙一样大眼睛的仆人开了门,爱丽丝注意到这两个仆人,都戴着涂了脂的假发。她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从树林里探出头来听。 鱼仆人从胳膊下面拿出一封很大的信,这信几乎有他身子那么大,然后把信递给那一个,同时还用严肃的声调说:“致公爵夫人:王后邀请她去玩槌球。”那位青蛙仆人只不过把语序变了一下,用同样严肃的声调重复着说:“王后的邀请:请公爵夫人去玩槌球。” 然后他们俩都深深地鞠了个躬,这使得他们的假发缠在一起了。这情景惹得爱丽丝要发笑了,她不得不远远地跑进树林里,免得被他们听到。她再出来偷看时,鱼仆人已经走了,另一位坐在门口的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愣神。 爱丽丝怯生生地走到门口,敲了门。 “敲门没用。”那位仆人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同你一样,都在门外,第二,他们在里面吵吵嚷嚷,根本不会听到敲门声。”确实,里面传来了很特别的吵闹声:有不断的嚎叫声,有打喷嚏声,还不时有打碎东西的声音,好像是打碎盘子或瓷壶的声音。 “那么,请告诉我,”爱丽丝说,“我怎么进去呢?” “如果这扇门在我们之间,你敲门,可能还有意义,”那仆人并不注意爱丽丝,继续说着,“假如,你在里面敲门,我就能让你出来。”他说话时,一直盯着天空,爱丽丝认为这是很不礼貌的。“也许他没有办法,”她对自己说,“他的两只眼睛几乎长到头顶上了,但至少是可以回答问题的,我该怎样进去呢?”因此,她又大声重复地说。 “我坐在这里,”那仆人继续说他的,“直到明天……” 就在这时,这个房子的门开了,一只大盘子朝仆人的头飞来,掠过他的鼻子,在他身后的一棵树上撞碎了。 “……或者再过一天。”仆人继续用同样的口吻说,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该怎么进去呢?”爱丽丝更大声地问, “你到底要不要进去呢?”仆人说,“要知道这是该首先决定的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不过爱丽丝不愿意承认这点,“真讨厌,”她对自己喃喃地说道,“这些生物讨论问题的方法真能叫人发疯。” 那仆人似乎认为是重复自己的话的好机会,不过稍微改变了一点儿说法:“我将从早到晚坐在这几,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 “可是我该干什么呢?”爱丽丝说,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仆人说服就吹起口哨来了。 “唉,同他说话没用!”爱丽丝失望地说,“他完全是个白痴!”然后她就推开门自己进去了。 这门直通一间大厨房,厨房里充满了烟雾,公爵夫人在房子中间,坐在—只三腿小凳上照料一个小孩。厨师俯身在炉子上的一只人锅里搅拌着,锅里好像盛满了汤。 “汤里的胡椒确实太多了!”爱丽丝费劲儿地对自己说,并不停地打着喷嚏。 空气里的胡椒味也确实太浓了,连公爵夫人也常常打喷嚏。至于那个婴孩,不是打喷嚏就是嚎叫,一刻也不停。这间厨房里只有两个生物不打喷嚏,就是女厨师和一只大猫,那只猫正趴在炉子旁,咧着嘴笑哩。 “请告诉我,”爱丽丝有点胆怯地问,因为她还不十分清楚自己先开口合不合规矩,“为什么你的猫能笑呢?” “它是柴郡猫(郡:英国的行政区域单位,柴郡为一个郡的名称,由于本书影响,现在西方人都把露齿傻笑的人称为柴郡猫。),”公爵夫人说,“这就是为什么它会笑了。猪!” 公爵夫人凶狠地说出的最后的—个字,把爱丽丝吓了一大跳。但是,爱丽丝马上发觉她正在同婴孩说话,而不是对自己说,于是她又鼓起了勇气,继续说: “我还不知道柴郡猫经常笑,实际上,我压根儿不知道猫会笑的。” “它们都会的,”公爵夫人说,“起码大多数都会笑的。” “我连一只都没见过。”爱丽丝非常有礼貌地说,并对这场开始了的谈话感到高兴。 “你知道的太少了,”公爵夫人说,“这是个事实。” 爱丽丝不喜欢这种谈话的口气,想最好换个话题,她正在想话题的时候,女厨师把汤锅从火上端开了,然后立即把她随手能拿着的每件东西扔向公爵夫人和婴孩。火钩子第一个飞来,然后,平底锅、盆子、盘子像暴风雨似地飞来了。公爵夫人根本不理会,甚至打到身上都没反应。而那婴孩早已经拼命地嚎叫了,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打到了他身上没有。 “喂,当心点!”爱丽丝喊着,吓得心头不住地跳,“哎哟,他那小鼻子完了。”真的,一只特大平底锅紧擦着鼻子飞过,差点就把鼻子削掉了。 “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公爵夫人嘶哑着嗓子嘟喷着说,“地球就会比现在转得快一些。” “这没好处,”爱丽丝说,她很高兴有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知识,“你想想这会给白天和黑夜带来什么结果呢?要知道地球绕轴转一回要用二十四个钟头。” “说什么?”公爵夫人说,“把她的头砍掉!” 爱丽丝相当不安地瞧了女厨师一眼,看她是不是准备执行这个命令,女厨师正忙着搅汤,好像根本没听到,于是爱丽丝又继续说:“我想是二十四个小时,或许是十二个小时,我……” “唉,别打扰我!”公爵夫人说,“我受不了数字!”她说着照料孩子去了,她哄孩子时唱着一种催睡曲,唱到每句的末尾,都要把孩子猛烈地摇儿下。 “对你的小男孩要粗暴地说话,在他打喷嚏的时候就读他,因为他这样只是为了捣乱,他只不过是在撒娇和卖傻。”合唱(女厨师和小孩也参加):哇!哇!哇! 公爵夫人唱第二段歌时,把婴孩猛烈地扔上扔下,可怜的小家伙没命地嚎哭,所以爱丽丝几乎都听不清唱词了:“我对我的小孩说话严厉,他一打喷嚏我就读他个够味,因为他只要高兴,随时可以欣赏胡椒的味道。”合唱:哇!哇!哇! “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抱他一会儿!”公爵夫人一边对爱丽丝说,一边就把小孩扔给她,“我要同王后玩链球去了,得准备一下。”说着就急忙地走出了房间。她往外走时,女厨师从后自向她扔了只炸油锅,但是没打着。 爱丽丝费劲儿地抓住那个小孩,因为他是个样子奇特的小生物,他的胳膊和腿向各个方向伸展,“真像只海星,”爱丽丝想,她抓着他时,这可怜的小家伙像蒸汽机样地哼哼着,还把身子一会儿蜷曲起来,一会儿伸开,就这样不停地折腾,搞得爱丽丝在最初的一两分钟里,只能勉强把他抓住。 她刚找到—种拿住他的办法(把他像打结一样团在一起,然后抓紧他的右耳朵和左脚,他就不能伸开了)时,就把他带到屋子外面的露天地方去了。“如果我不把婴孩带走,”爱丽丝想,“她们肯定在一两天里就会把他打死的。把他扔在这里不就害了他吗?”最后一句她说出声来了,那小家伙咕噜了一声作为回答(这段时间他已经不打喷嚏了)。别咕噜,”爱丽丝说,“你这样太不像样子了。” 那婴孩又咕噜了一声,爱丽丝很不安地看了看他的脸,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他鼻子朝天,根本不像个常人样,倒像个猪鼻子;他的眼睛也变得很小不像个婴孩了。爱丽丝不喜欢这副模样。“也许他在哭吧,”爱丽丝想。她就看看他的眼睛,有没有眼泪。 没有,一点儿眼泪也没有。“如果你变成了一只猪,”爱丽丝严肃地说,“听着,我可再不理你了!”那可怜的小家伙又抽泣了一声(或者说又咕噜了—声,很难说到底是哪种),然后他们就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爱丽丝正在想:“我回家可把这小生物怎么办呢?,这时,他又猛烈地咕噜了一声,爱丽丝马上警觉地朝下看他的脸。这次一点儿都不会错了,它完全是只猪。她感到如果再带着它就太可笑了。 于是她把这小生物放下,看着它很快地跑进树林,感到十分轻松。“如果它长大的话,爱丽丝对自己说,“一定会成为可怕的丑孩子,要不就成为个漂亮的猪。”然后,她去一个个想她认识的孩子,看看谁如果变成猪更像样些,她刚想对自己说:“只要有人告诉他们变化的办法……”,这时,那只柴郡猫把她吓了一跳,它正坐在几码远的树枝上。 猫对爱丽丝只是笑,看起来倒是好脾气。爱丽丝想,不过它还是有很长的爪子和许多牙齿,因此还应该对它尊敬点。 “柴郡猫,”她胆怯地说。还不知道它喜欢不喜欢这个名字,可是,它的嘴笑得咧开了。“哦,它很高兴,”爱丽丝想,就继续说了:“请你告诉我,离开这里应该走哪条路?” “这要看你想上哪儿去,”猫说。 “去哪里,我不大在乎。”爱丽丝说。 “那你走哪条路都没关系。”猫说。 “只要.能走到一个地方。”爱丽丝又补充说了一句。 “哦,那行,”猫说,“只要你走得很远的话。” 爱丽丝感到这话是没法反对的,所以她就试着提了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周围住些什么?” “这个方向”猫说着,把右爪子挥了一圈,“住着个帽匠;那个方向,”猫又挥动另一个爪子,“住着一只三月兔。你喜欢访问谁就访问谁,他们俩都是疯子。” “我可不想到疯子中间去。”爱丽丝回答。 “啊,这可没法,”猫说,“我们这儿全都是疯的,我是疯的,你也是疯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的?”爱丽丝问。 “一定的,”猫说,“不然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爱丽丝想这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她还是继续问:“你又怎么知遏你是疯子呢?” “咱们先打这里说起,”猫说,“狗是不疯的,你同意吗?” “也许是吧!爱丽丝说。 “好,那么,”猫接着说,“你知道,狗生气时就叫,高兴时就摇尾巴,可是我,却是高兴时就叫,生气时就摇尾巴。所以,我是疯子。” “我把这说成是打呼噜,不是叫。”爱丽丝说。 “你怎么说都行,”猫说,“你今天同王后玩槌球吗?” “我很喜欢玩槌球,”爱丽丝说,“可是到现在还没有邀请我嘛!” “你,会在那儿看到我!”猫说着突然消失了。 爱丽丝对这个并不太惊奇,她已经习惯这些不断发生的怪事了。她看着猫坐过的地方,这时,猫又突然出现了。 “顺便问一声,那个婴孩变成什么了?”猫说,“我差一点忘了。” “已经变成一只猪了。”爱丽丝平静地回答说,就好像猫再次出现是正常的。 “我就想它会那样的。”猫说着又消失了。 爱丽丝等了一会,还希望能再看见它,可是它再没出现。于是,她就朝着三月兔住的方向走去。“帽匠那儿,我也要去的。”她对自己说,“三月兔一定非常有趣,现在是五月,也许它不至于太疯——至少不会比三月份疯吧。”就在说这些话时,一抬头又看见那只猫,坐在一根树枝上。 “你刚才说的是猪,还是竹?”猫问。 “我说的是猪,”爱丽丝回答,“我希望你的出现和消失不要太突然,这样,把人搞得头都晕了。” “好,”猫答应着。这次它消失得非常慢,从尾巴尖开始消失,一直到最后看不见它的笑脸,那个笑脸在身体消失后好久,还停留了好一会儿。 “哎哟,我常常看见没有笑脸的猫,”爱丽丝想,“可是还从没见过没有猫的笑脸呢。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儿了。” 她没走多远,就见到了一间房子,她想这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了,因为烟囱像长耳朵,屋顶铺着兔子毛。房子很大,使她不敢走近。她咬了口左手的蘑菇,使自己长到了二英尺高,才胆怯地走去,一边对自己说:“要是它疯得厉害可怎么办?我还不如去看看帽匠呢!” 第七章 发疯的茶会 房前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和帽匠坐在桌旁喝着茶,一只睡鼠在他们中间酣睡着,那两个家伙把它当做垫子,把胳膊支在睡鼠身上,而且就在它的头上谈话。“这睡鼠可够不舒服的了,”爱丽丝想,“不过它睡着了,可能就不在乎了。” 桌子很大,他们三个都挤在桌子的一角,“没地方啦!没地方啦!”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就大声嚷着。 “地方多得很呢!”爱丽丝说着就在桌子一端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 “要喝酒吗?”三月兔热情地问。 爱丽丝扫视了一下桌上,除了茶,什么也没有。“我没看见酒啊!”她回答。 “根本就没酒嘛!”三月兔说。 “那你说喝酒就不太礼貌了。”爱丽丝气愤地说。 “你没受到邀请就坐下来,也是不太礼貌的。”三月兔回敬她。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爱丽丝说,“这可以坐下好多人呢?还不止三个!” “你的头发该剪了。”帽匠好奇地看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你应该学会不随便评论别人,”爱丽丝板着脸说,“这是非常失礼的。” 帽匠睁大眼睛听着,可是末了他说了句:“一只乌鸦为什么会像一张写字台呢?” “好了,现在我们可有有趣的事了!”爱丽丝想,“我很高兴猜谜语,我一定能猜出来,”她大声说。 “你的意思是你能说出答案来吗?”三月兔问, “正是这样。”爱丽丝说。 “那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三月兔继续说。 “我正是这样的,”爱丽丝急忙回答,“至少……至少凡是我说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回事,你知道。” “根本不是一回事,”帽匠说,“那么,你说‘凡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凡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能吃’,也算是一样的了?”三月兔加了句:“那么说‘凡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凡是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我的’,也是一样的喽?” 睡鼠也像在说梦话一样说道:“那么说‘我睡觉时总要呼吸’和‘我呼吸时总在睡觉’也是一样的吗?” “这对你倒真是一个样。”帽匠对睡鼠说。谈到这里话题中断了,大家沉默了一会,这时候爱丽丝费劲儿地想着有关乌鸦和写字台的事,可是她知道的确实不能算多,还是帽匠打破了沉默,“今天是这个月的几号?”他问爱丽丝,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看着,还不停地摇晃,拿到耳朵旁听听。 爱丽丝想了想说,“四号。” “错了两天!”帽匠叹气说,“我告诉你不该加奶油的,”他又生气地看着三月兔加了一句。 “这是最好的奶油了!”三月兔辩白地说。 “不错,可是不少面包屑也掉进去了,帽匠咕噜着,“你不应该用面包刀加奶油。” 三月兔泄气地拿起怀表看看,再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看,但是除了说“这是最好的奶油了”,再没别的说的了。 爱丽丝好奇地从他肩头上看了看。“多么奇怪的不表啊,”她说,“它告诉几月几日,却不告诉时间。” “为什么要告诉时间呢?”帽匠嘀咕着,“你的表告诉你哪一年吗?” “当然不,”爱丽丝很快地回答说,“可是很长时,里年份不会变的。” “这也跟我的表不报时间的原因一样。”帽匠说。 爱丽丝被弄得莫名其妙,帽匠的话听起来没有任何意思,然而确实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话。“我不大懂你的话,”她很礼貌地说。 “睡鼠又睡着了,”帽匠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一点热茶。 睡鼠立即晃了晃头,没睁开眼就说:“当然,当然,我自己正要这么说呢。” “你猜到那个谜语了吗?”帽匠说爱丽丝,“没有,我猜不出来,”爱丽丝回答,“谜底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帽匠说。 “我也不清楚,”三月兔说, 爱丽丝轻轻叹了一声说,“我认为你应该珍惜点时间,像这样出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简直是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对时间熟悉,”帽匠说,“你就不会叫它‘宝贵的时间’,而叫它‘老伙计’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爱丽丝说。 “你当然不懂,”帽匠得意地晃着头说,“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同时间说过话。” “也许没有,”爱丽丝小心地回答,“但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总是按着时间打拍子的。” “唉,这就完了!”帽匠说,“你最不高兴人家按住它打了。如果你同它好,它会让钟表听你的话,譬如说,现在是早上九点钟,正是上学的时间,你只要悄悄地对时间说一声,钟表就会一下子转到一点半,该吃午饭了!” “我真希望这样。”三月兔小声自语道。 “那太棒了!”爱丽丝思索着说,“可是要是我还不饿怎么办呢?” “一开始也可能不饿,”帽匠说,“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保持在一点半钟。” “你是这样办的吗?”爱丽丝问。 帽匠伤心地摇摇头,“我可不行了,”他回答,“我和时间在三月份吵了架——就是他发疯前(他用茶匙指着三月兔),那是在红心王后举办的一次大音乐会上,我演唱了: ‘闪闪的小蝙蝠,我感到你是多么奇怪!’ 你可能知道这首歌吧?” “我听过一首同它有点像(原来的歌应为“闪闪的小星,你是多么的奇怪……帽匠全唱错了。这首歌现在中国有唱片,有些中小学常常播放。)。”爱丽丝说。 “我知道下面是这样接着的,”帽匠继续说,“是这样的: ‘你飞在地面上多高, 就像茶盘在天空上。 闪啊,闪啊……’” 睡鼠抓了摇身子,在睡梦中开始唱道:“闪啊,闪啊,闪啊,闪啊,”一直唱下去,直到他们捅,了它一下才停止。 “我还没唱完第一段,”帽匠说,“那王后就大喊道“他简直是在糟蹋时间,砍掉他的头!’” “多么残忍呀!”爱丽丝攘道。 帽匠伤心地继续说,“从那以后,它就再也不肯照我的要求做了,它总是停在六点钟。” 爱丽丝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聪明的念头,她问:“这就是这儿有这么多茶具的缘故吗?” “是的,就是这个缘故,”帽匠叹息着说,“只有喝茶的时间,连洗茶具的时间也没有了。”, “所以你们就围着桌子转?”爱丽丝问。 “正是这样,”帽匠说,“茶具用脏了,我们就往下挪。” “可是你们转回来以后怎么办呢?”爱丽丝继续间。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三月兔打着哈欠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我听烦了,建议让小姑娘讲个故事吧。” “恐怕我一个故事都不会讲,”爱丽丝说。她对这个建议有点慌神。 “那么睡鼠应该讲一个!”三月兔和帽匠一齐喊道,“醒醒,睡鼠!”他们立刻在两边一起捅它。 睡鼠慢慢地睁开眼,嘶哑无力地说:“我没有睡,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着呢。” “给我们讲个故事!”三月兔说。 “就是,请讲一个吧!”爱丽丝恳求着。 “而且要快点讲,要不然你还没讲完又睡着了,”帽匠加了一句。 睡鼠急急忙忙地讲了:“从前有三个小姐妹,她们的名字是:埃尔西、莱斯、蒂尔莉,她们住在一个井底下……” “她们靠吃什么活着呢?”爱丽丝总是最关心吃喝的问题。 “她们靠吃糖浆生活。”睡鼠想了一会儿说。 “你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她们都会生病的。”爱丽丝轻声说。 “正是这样,她们都病了,病得很厉害。”睡鼠说。 爱丽丝尽量地想象这样特殊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子,可是太费脑子了。于是,她又继续问:“她们为什么要住在井底下呢?” “再多喝一点茶吧!”三月兔认真地对爱丽丝说。 “我还一点都没喝呢?因此不能说再多喝一点了!”爱丽丝不高兴地回答。 “你应该说不能再少喝点了,”帽匠说,“比没有喝再多喝一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没人来问你!”爱丽丝说。 “现在是谁失礼了?”帽匠得意地问。 这回爱丽丝不知该说什么了,只得自己倒了点茶,拿了点奶油面包,再向睡鼠重复她的问题:“她们为什么要住在井底下呢?”, 睡鼠又想了一会,说:“因为那是一个糖浆井。” “没有这样的井!”爱丽丝认真了。帽匠和三月兔不停地发出“嘘、嘘……”的声音,睡鼠生气地说:“如果你不讲礼貌,那么最好你自己来把故事讲完吧。” “不,请你继续讲吧!”爱丽丝低声恳求着说,“我再不打岔了,也许有那样一个井吧。” “哼,当然有一个!”睡鼠煞有介事地说。又往下讲了:“这三个小姐妹学着去画画。” “她们画什么呢?”爱丽丝忘了自己的保证又问开了。 “糖浆。”睡鼠这次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想要一只干净茶杯,”帽匠插嘴说,“让我们移动一下位子吧。” 他说着就挪到了下一个位子上,睡鼠跟着挪了,三月兔挪到了睡鼠的位子上,爱丽丝很不情愿地坐到了三月兔的位子上。这次挪动唯一得到好处的是帽匠,爱丽丝的位子比以前差多了,因为三月兔把牛奶罐打翻在位子上了。 爱丽丝不愿再惹睡鼠生气,于是开始小心地说:“可是我不懂,她们从哪里把糖浆取出来的呢?” “你能够从水井里吸水,”帽匠说,你也应该想到从糖浆井里能够吸糖浆了,怎么样,傻瓜?” “但是她们在井里呀!”爱丽丝对睡鼠说。 “当然她们是在井里啦,”睡鼠说,“还在很里面呢。” 这个回答把可怜的爱丽丝难住了,她好大没打搅睡鼠,让它一直讲下去。 “她们学着画画,”睡鼠继续说着,一边打了个哈欠,又揉揉眼睛,已经非常困了,“她们画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每件东西都是用‘老’宇开头的。” “为什么用‘老’字开头呢?”爱丽丝问。 “为什么不能呢?”三月兔说。 爱丽丝不吭气了。这时候,睡鼠已经闭上了眼,打起盹来了,但是被帽匠捅了—下,它尖叫着醒来了,继续讲,“用‘老’字开头的东西,例如老鼠笼子,老头儿,还有老多。你常说老多东西,可是你怎么画出这个—老多’来?” “你问我吗?”爱丽丝难住了,说,“我还没想……” “那么你就不应该说话!”帽匠说。 这句话可使爱丽丝无法忍受了,于是她愤愤地站起来走了,睡鼠也立即睡着了。那两个家伙一点也不注意爱丽丝的走掉。爱丽丝还回头看了一两次,指望他们能够留她。后来她看见他们正要把睡鼠塞进茶壶里去。 “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去那里了,”爱丽丝在树林中找路时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茶会了。” 就在她叨叨咕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棵树上还有一个门,可以走进去。“真奇怪!”她想,“不过今天的每件事都很奇怪,还是进去看看吧。”想着就走进去了。 她又一次来到那个很长的大厅里了,而且很靠近那只小玻璃桌子。“啊,这是我最好的机会了!”她说着拿起了那个小金钥匙,打开了花园的门,然后轻轻地咬了一门蘑菇(她还留了一小块在口袋里呢),直到缩成大约一英尺高,她就走过了那条小过道。终于进入了美丽的花园,到达了漂亮的花坛和清凉的喷泉中间了。 第八章 王后的槌球场 靠近花园门口有一棵大玫瑰树,花是白色的,三个园丁正忙着把白花染红。爱丽丝觉得很奇怪,走过去想看看。当她正朝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小心点,老五!别这样把颜料溅到我身上。” “不是我不小心,”老五生气地说,“是老七碰了我的胳膊。” 这时老七抬起头说:“得啦!老五,你老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你最好别多说了,”老五说,“我昨天刚听王后说,你该受斩头的惩罚!” “为什么?”第一个说话的人问。 “这与你无关,老二!”老七说。 “不,与他有关!”老五说,“我要告诉他——这是由于你没给厨师拿去洋葱,而拿去了郁金香根!” 老七扔掉了手上的刷子说,“哦,说起不公平的事……”他突然看到了爱丽丝,爱丽丝正站着注视他们呢。他随即不说了,那两个也回过头来看。然后三人都深深地鞠了一躬。 “请你们告诉我,”爱丽丝胆怯地说,“为什么染玫瑰花呢?” 老五和老七都望着老二,老二低声说:“哦,小姐,你知道,这里应该种红玫瑰的,我们弄错了,种了白玫瑰,如果王后发现,我们全都得被杀头。小姐,你看,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要在王后驾临前,把……”就在这时,一直在焦虑地张望的老五,突然喊道:“王后!王后!”这三个园丁立即脸朝下地趴下了。这时传来了许多脚步声,爱丽丝好奇地审视着,想看看王后。 首先,来了十个手拿狼牙棒的士兵,他们的样子全都和三个园丁一样,都是长方形的平板,手和脚长在板的四角上。接着来了十名侍臣,这些人全都用钻石装饰着,像那些士兵一样,两个两个并排着走。侍臣的后面是王室的孩子们,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一对对手拉着手愉快地跳着跑来了,他们全都用红心(红心和侍臣的钻石,士兵的狼牙棒,是纸牌中的三种花色。即:红桃、方块、草花,英文原意为红心、钻石、棒子。)装饰着。后面是宾客,大多数宾客也是国王和王后。在那些宾客中,爱丽丝认出了那只白兔,它正慌忙而神经质地说着话,对别人说的话都点头微笑,却没注意到爱丽丝。接着,是个红心武士,双手托着放在紫红色垫子上的王冠。这庞大的队伍之后,才是红心国王和王后。 爱丽丝不知道该不该像那三个园丁那样,脸朝地的趴下,她根本不记得王室行列经过时,还有这么一个规矩。“人们都脸朝下趴着,谁来看呢?这样,这个行列有什么用呢?”也这样想着,仍站在那里,等着瞧。 队伍走到爱丽丝面前时,全都停下来注视着她。王后严厉地问红心武上:“这是谁呀!”红心武士只是用鞠躬和微笑作为回答。 “傻瓜!”王后不耐烦地摇摇头说,然后向爱丽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孩?” “我叫爱丽丝,陛下。”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可她又自己嘀咕了句:“哼!说来说去,他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用不着怕他们!” “他们是谁呢?”皇后指着三个园丁问。那三个园丁围着一株玫瑰趴着,背上的图案同这副纸牌的其他成员一样,看不出这三个是园丁呢?还是士兵、侍臣,或者是她自己的三个孩子了。 “我怎么知道呢?这不干我的事!”爱丽丝回答,连她自己都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惊奇。 王后的脸气红了,两眼像野兽样瞪了爱丽丝一会儿,然后尖声叫道:“砍掉她的头!砍掉……” “废话!”爱丽丝干脆大声说。而王后却不说话了。 国王用手拉了下王后的胳膊,小声地说:“冷静点,我亲爱的,她还只是个孩子啊!” 王后生气地从国王身边转身走开了,并对武士说:“把他们翻过来。” 武士用脚小心地把他们三个翻了过来。 “起来!”王后尖声叫道。那三个园丁赶紧爬起来,开始向国王、王后、王室的孩子们以及每个人一一鞠躬。 “停下来!”王后尖叫着,“把我的头都弄晕了!”她转身向着那株玫瑰继续问:“你们在于什么?” “陛下,愿你开恩,”老二低声下气地跪下一条腿说,“我们正想……” “我明白了!砍掉他们的头!,王后察看了一阵玫瑰花后说。队伍又继续前进了,留下三个士兵来处死这三个不幸的园丁。三个园丁急忙跑向爱韶丝,想得到她的保护。 “你们不会被砍头的!”爱丽丝说着就把他们藏进旁边的一个大花盆里。那三个士兵到处找,几分钟后还没找到,只得悄悄地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了。 “把他们的头砍掉没有?”王后怒吼道。 “他们的头已经掉了,陛下!”士兵大声回答, “好极了!”王后说,“你会玩槌球吗?” 士兵们都看着爱丽丝,这个问题显然是问爱丽丝的。 “会!”爱丽丝大声回答。 “那就过来!”王后喊道。于是爱丽丝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她心里盘算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这真是一个好天气呵!”爱丽丝身旁一个胆怯的声音说。原来爱丽丝恰巧走在白兔的旁边,白兔正焦急地偷愉看着她的脸呢。 “是个好天气,”爱丽丝说,“公爵夫人在哪里呢?” “嘘!嘘!”兔子急忙低声制止她,同时还担心地转过头向王后看看,然后踮起脚尖把嘴凑到爱丽丝的耳朵根上,悄悄地说:“她被判处了死刑。” “为什么呢?”爱丽丝问。 “你是说真可怜吗?”兔子问。 “不,不是,”爱丽丝问,“我没想可怜不可怜的问题,我是说为什么?” “她打了王后耳光……”兔子说。爱丽丝笑出声来了。“嘘!”兔子害怕地低声说,“王后会听到的!你知道,公爵夫人来晚了,王后说……” “各就各位!”王后雷鸣般地喊了一声,人们就朝各个方向跑开了,撞来撞去的,一两分钟后总算都站好了自己的位置。于是游戏开始了。 爱丽丝想,可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奇怪的槌球游戏呢?球场到处都是坎坷不平的,槌球是活刺猬,槌球棒是活红鹤(红鹤:Phoenicopterus科,趾间有蹼,因种不同羽色各异,有红、灰等色。虽称红鹤,但与鹤科Gruidae无关。中国无此鸟。),士兵们手脚着地当球门。 起初,爱丽丝很难摆弄红鹤,后来总算很成功地把红鹤的身子舒服地夹在胳膊底下,红鹤的腿垂在下面。可是,当她好不容易把红鹤的脖子弄直,准备用它的头去打那个刺猬时,红鹤却把脖子扭上来,用奇怪的表情看着爱丽丝的脸,惹得爱丽丝大声笑了。她只得把红鹤的头按下去,当她准备再一次打球的时候,恼火地发现刺猬已经展开了身子爬走了。此外,把刺猬球打过去的路上总有一些土坎或小沟,躬腰做球门的士兵常常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其它地方去。爱丽丝不久就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 参加游戏的人没等轮到自己,就一起打起球来了,不时地为了刺猬争吵和打架。不一会,王后就大发雷霆,跺着脚来回地走,大约一分钟叫喊一次:“砍掉他的头!”“砍掉她的头!” 爱丽丝感到非常不安,说真的她还没有同王后发生争吵,可是这是每分钟都可能发生的呀!“如果吵架的话,”她想,“我会怎么样呢?这儿的人太喜欢砍头了!可是很奇怪,现在还有人活着。” 爱丽丝就寻找逃走的路,而且还想不被人发现的逃开。这时,她注意到天空出现了一个怪东西,起初她惊奇极了,看了一两分钟后,她判断出这是一个笑容,并对自己说:“这是柴郡猫,现在我可有人说话了。” “你好吗?”柴郡猫刚出现了能说话的嘴就问。 爱丽丝等到它的眼睛也出现了,才点点头。“现在跟它说话没用处,”她想,“应该等它的两只耳朵也来了,至少来,了一只,再说话。”过了一两分钟,整个头出现了,爱丽丝才放下红鹤,给它讲打槌球的情况。她对于有人听她说话非常高兴。那只猫似乎认为出现的部分已经够了,就没有显露出身子。 “他们玩得不公平,”爱丽丝抱怨地说,“他们吵得太厉害了,弄得人家连自己说的话都听不清了。而且他们好像没有一定的规则,就算有的话,也没人遵守。还有,你简直想象不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真讨厌。譬如说,我马上就要把球打进球门,而那个球门却散步去了;再加我正要用自己的球碰王后的刺猾球,哼,它一见我的球来撒腿就跑掉啦!” “你喜欢王后吗?”猫轻声说。 “一点都不喜欢,”爱丽丝说,“她非常……”正说到这里,她突然发觉王后就在她身后听呢?于是她马上改口说:“非常会玩椒球,别人简直不必要再同她比下去了。” 王后微笑着走开了。 “你在跟谁说话?”国王走来问爱丽丝,还很奇怪地看着那个猫头。 “请允许我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爱丽丝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它的模样,不过,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吻我的手。”国王说。 “我不愿意。”猫回答。 “不要失礼!”国王说,“别这样看我了!”他一边说一边躲到爱丽丝的身后。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一本书上见过这句话,不过不记得是哪本书了。”爱丽丝说。 “喂,必须把这只猫弄走!”国王坚决地说,接着就向刚来的王后喊道:“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来把这只猫弄走。” 王后解决各种困难的办法只有一种:“砍掉它的头!”她看也不看一下就这样说。 “我亲自去找刽子手。”国王殷勤地说着,急急忙忙走了。 爱丽丝听到王后在远处尖声吼叫,想起该去看看游戏进行得怎样了。爱丽丝已经听到王后又宣判了三个人死刑,原因是轮到他们打球而没有马上打。爱丽丝很不喜欢这个场面,整个游戏都是乱糟糟的,弄得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什么时候不轮到。因此她就走了,找她的刺猬去了。 她的刺猬正同另一只刺猬打架,爱丽丝认为这真是用一只刺猬球去打中另一个刺猬球的好机会,可是她的红鹤却跑掉了,爱丽丝看到它正在花园的那边,在徒劳地向树上飞。 等她捉住红鹤回来,正在打架的两只刺猬都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想:“这没多大关系,因为这里的球门都跑掉了。”为了不让红鹤再逃跑,爱丽丝把它夹在胳膊下,又跑回去想同她的朋友多谈一会儿。 爱丽丝走回柴郡猫那儿时,惊奇地看到一大群人围着它,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在激烈地辩论。他们同时说话,而旁边的人都静悄悄地呆着,看上去十分不安。 爱丽丝刚到,这三个人就立即让她作裁判,他们争先恐后地同时向她重复自己的理由,爱丽丝很难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 刽子手的理由是:除非有身子,才能从身上砍头,光是一个头是没法砍掉的。他说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这辈子也不打算做这样的事了。 国王的理由是:只要有头,就能砍,你刽子手执行就行了,少说废话。王后的理由是:谁不立即执行她的命令,她就要把每个人的头都砍掉,周围的人的头也都砍掉(正是她最后这句话,使这些人都吓得要命)。 爱丽丝想不出什么办法,只是说:“这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最好去问她。” “她在监狱里,”王后对刽子手说,“把她带来!”刽子手好像离弦的箭似的跑去了。 就在刽子手走去的一刹那,猫头开始消失,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来到时,猫头完全没有了。国王和刽子手就发疯似地跑来跑去到处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槌球了。